 手机访问:wap.265xx.com
手机访问:wap.265xx.com怎么评价上野千鹤子的《厌女》?
这本书我看过了,我简单罗列了一下它本身的问题——从根源上抹黑马克思主义,将其狭隘化、曲解化,并用新自由主义进行重新包装(即白左化)。扩大了“女性嫌恶”的概念范围,将矛头指向了包括亲人和陌生人在内的所有人。在明确指出拒绝“厌女”的同时,使用歧视性语言“厌男”,属于两面三刀的双重标准。她的言论也压根不顾及人的多元化问题。她的这方面的研究在日本社会这样的小国寡民、极端威权的模式下,有少量的对于日本右翼的正确性和进步性。但该思想和言论不适用于外传。理论脱离群众基础,以城市白领阶层为基本盘亦服务于城市白领阶层,故对于普通劳动者没有指导意义。
简单说说这些条目——上野千鹤子污蔑马克思主义是“只完全解放男人的思想学说”。首先,马克思主义是哲学范畴,本质上是要让人认清世界、社会的模式和基本发展逻辑。科学社会主义才是解放人类的学说。“女性嫌恶”在mgtow哲学体系下可以解读为——因为对于女性这一中心性别付出得不够或者挑战其权威的想法或行为。你大概猜一下这个东西是什么性质的。用常规人的理解来说,“女性嫌恶”具体为封建思想的遗留。这一点有些回答已经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下,不讨论人性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性是过于抽象的表述,因此它必须是具体的、客观存在的表述。也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认为有通用的人性,只有在某种社会制度下,某个阶级有怎样的整体性格特点,在这样的社会下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不适用于外传主要就是因为日本的思想在二战结束至50年代末期处于真空状态,这导致了日本压根没有精神支柱,故日本韩国的情况比较通用。而中国地大物博,客观上形成了宗族豪强这样的长期大型力量,所以中国人天然地和民族、国籍和土地捆绑,国情完全不同。之所以说理论脱离群众基础,最简单的问题就在于她没想好要团结谁,也没想好怎么团结。统战价值和队伍纯洁性的平衡必须要把握好。举目四望面面是敌和队伍臃肿尾大不掉都是足以造成失败的因素。就算只以同类这个阶层来表述拟合,在忽略雌竞和人际博弈的条件下也不具备实践的能力和渠道。
《厌女》这本书还没有读完,但我曾看到上野千鹤子老师另一本书里提到一个观点:其实在我看来,人们挂在嘴边的所谓恋爱本就很牵强,因为一方是通过少女漫画学习恋爱的女人,另一方则是通过 AV 学习性的男人,这样两个人要在不同的语境下“分享”同一个空间,想方设法将对方拽进自己的语境,这未免也太强人所难了。您在信中以《死之棘》为例,指出“在恋爱这种游戏中,女人的赌注和男人的赌注从来都不对等”。要我说,那岂止是不对等,根本是完全不同。 AV 中的女演员是男人的玩具,但在少女漫画中,爱情是满足认可欲求的唯一工具。——《始于极限》[日]上野千鹤子
这个观点,依旧是部分群体的老生常谈,即:女人喜欢男人,是对强权的服从;男人喜欢女人,是征服欲作祟。
对于该类观点,我一贯持反对态度,反驳起来其实也很容易:爱情从来不是AV影片和少女漫画的共生物或者伴生物。异性之间的爱情是人类百万年的进化结果,是建立在异性之间价值互补性的基础之上的繁衍本能,是神经递质和激素调节人类的情绪、情感和行为的产物。女人喜欢男人,正如男人喜欢女人,爱情属于本能范畴,更是人类道德与文明的产物。
换句话说,难道在AV影片和少女漫画出现之前,或者说与影片漫画同等类型事物如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牛郎织女等民间传说出现之前,就没有爱情了吗?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上野千鹤子的《厌女》,也许对女性平权运动有一定的积极的借鉴抑或指导意义,但就上面这个观点而言,太过浅薄和偏颇,应该辩证地、带有怀疑和警惕的态度去读。
引子
1997年3月19日,位于东京涩谷区圆山町一栋叫做“喜寿庄”的旧式木造建筑公寓内,发现了一具女尸,死者为当地常见的一名当街揽客的站街女。原本这一则新闻属于繁华都市阴影下的寻常恶性事件,但当警方再次核对死者身份的时候,惊讶地发现这名原本属于社会最底层的性工作者,在白天还有光鲜亮丽的另一个身份——毕业于应庆大学的高材生,现就职于东京电力公司,任规划部经济研究处副处长的渡边泰子。要知道东京电力公司副长职位的年薪约一千万日元左右,而涩谷区的站街女接一次客只有不到两千日元的收入。随着调查的深入,人们发现这位39岁的高层白领已经有6年的接客经历,并且包括她母亲在内的家人也知道期间她的所作所为。阳光之下端坐办公室的女性管理者,在夜幕来临后化身暗娼“夜莺”,这种强烈的角色反差,引起了日本社会广泛而持久的讨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东电女职员被杀事件”。
而在《厌女》一书中,加藤千鹤子也用了两章的篇幅论述了,由东电女职员事件所衍生和发散的关于日本社会的“厌女症”。上野千鹤子,日本著名的社会学家和女性学专家。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还处于繁荣阶段,同时经过了先前左翼学生运动的铺垫,女性运动热度空前高涨,此时上野开始登上舞台,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内。而此书著成于2010年左右,世界已经进入了全新的时代,女性运动也赋予了更多的色彩。有趣的是上野在后记中提到,这是一本著者写得不愉快,读者读着也不愉快的书,但无论有多么的不愉快,她都不得不面对现实,用文字向大众曝光那些如同附着在现代社会里,如同“结痂”般的东西。
面对著者的劝诫,身为男性的我为何执意去阅读一本女性主义的代表作呢?首先它是一本有趣的书,尽管作为书中的重点批判对象——成年男性,这份体验难免会引起自身对作者观点的怀疑、批判、辩解和否定,就像对着镜子检查衣物着装一样,心想“我才不是这样的人”。但我想说的是,正是有一份“不服气”的心态,才让自己怀有好奇心,坚持阅读下去,探究作者到底想要表述什么东西。而阅读社科类的书籍,我不会去选择那些完全顺着自己思路的读物,那样只会让我陷入更深的信息茧房,适当的背道而驰,可以拓宽自己的阅读边界。另外,上野书中的“厌女症”并非狭义的男性对女性的厌恶,而是用十六章的篇幅,以日本社会为背景,从更广义的角度去剖析厌女症的林林总总。这里面包括了,母亲对女儿的厌女症,女人之间的厌女症,社会层面的厌女症,甚至男性之间的厌女症。所以书中所表达出的女性主义也并非对标国内网络中矛盾日益激化的所谓“女权”主义,而是更深奥的社会性问题。当你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书中的观点和现象可以映射到更多的领域,诱发更多的思考。
正文
那么何为厌女症?上野开篇就从文学的角度进行解构,她提到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19世纪西方国家对于东方文化是没有太多真实根据,是凭空臆想出来的东方。而东方主义具有代表性的文艺作品就是意大利剧作家普契尼创作歌剧《蝴蝶夫人》,故事讲述了一名驻日美军军官在当地迎娶了一位日本新娘——蝴蝶,军官在婚后受调令回国,留下蝴蝶独守空房,三年后军官携美国正妻回到日本,蝴蝶知道后悲痛欲绝,殉情而亡。《蝴蝶夫人》的故事成为了这类悲剧爱情的范本,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更多的文艺作品,比如美籍华裔明星尊龙出演的《蝴蝶君》,以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黑石一雄在《远山淡影》中都有类似的故事重现。
但上野对这样的爱情经典不屑一顾,她认为东方主义就是西方男人的自慰品,对蝴蝶沉溺于“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你一定回来接我”——这样的桥段感到作呕。与其说是蝴蝶对美国军官丈夫的幻想,不如说是以普契尼这样的西方男性对东方女性的幻想。没有什么能比“在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国度,有一位美丽的的女人曾与我山盟海誓”——更能满足男人的虚荣心。当然,更进一步思考,这样的爱情桥段男女角色背负的是殖民时代强权西方世界对羸弱东方世界霸凌的隐喻,所以上野完全不明白那些为《蝴蝶夫人》鼓掌喝彩的日本观众的心思。
这样不对等的男女关系不仅存在于不同的文明世界,即使在相同的环境中,由于根深蒂固的历史遗留观念,男女性别的差异也同样体现在日本文化中。本书第一章,上野就提到了两位日本文坛的浪子——吉行淳之介和永井荷风。有趣的是,上野对吉行抱有敌视的态度,尽管他俩没有直接的文笔交锋,但是吉行的读者以骚扰的口吻对上野说:“去读吉行!读了你就懂得女人。”这是比较讽刺的事情,上野身为女人需要读男性作家吉行的那些描写娼妓世界的小说,才能明白什么是女人。所以上野认为吉行和永井这类作家的小说,如同东方主义的《蝴蝶夫人》,是男人对女人的幻想。
那么为何男性如此执着于对女性的幻想呢?上野一针见血地指出男人明明知道娼妓是为了钱,可又偏偏想去证明钱之外的“情”,娼妓的“不幸身世”不过是太常见的一种技巧。因此那些“不幸身世”和引发“不幸身世”的情节,就成了艺术创作者眼中的绝佳素材。
再发散一下,在海的彼岸,文脉同宗的华夏,文人墨客们似乎也深谙此道。混迹于青楼酒肆,“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柳永柳七公子,在死后由他的粉黛知己们筹钱安葬,这样的桥段也为后世那些风流文化的追随者所推崇。所以我们能看到诗词戏曲中多如牛毛的公子佳人,才子歌女,甚至发展到赶考进士和古寺女鬼的超越自然的爱情故事。按上野的逻辑,也算是男人对女性臆想的巅峰之作了。如果我们把宁采臣和聂小倩的身份对调一下——一位过路村妇与荒野雄怪的缠绵悱恻,这样的设定会让我们如鲠在喉,回忆一下《西游记》中的黄袍怪和百花羞公主,凡女怪男的搭配必然得不到世人的认可和祝福,某种程度上,文艺作品也反应了当世的男女关系。
如此的双重标准不仅体现在男女关系上,也体现在女性的不同角色上。前面我们提到了如此多的娼妓青楼文化,但当那些风流嫖客们遇到了带孩子的娼妓,就会因为女性角色上的矛盾而扫兴,“母亲”和“娼妓”在旧时代女性身上很常见的双重身份,在男人的精神世界中是万万不能混为一谈的,否则就会引发他们世界观的崩塌。
上野继续剖析,在近代给亚洲带来重大灾难的日本侵掠战争,其臭名昭著的“慰安妇”就是对日本男性强权社会的真实写照,所谓“慰安”显然是慰男人之安,对慰安妇而言,那是地狱般的奴隶劳动。但战争中的另一类女性“后方的妻子”又被国家舆论以道德的名义,架在了高处不胜寒的位置,她们被国防妇人会所监视,严格控制其与其他男性的往来。尽管她们也知道被征召作为士兵的丈夫,也许在某时某地和某位慰安妇做苟合之事,但在“大东亚共荣圈圣战”的绝对政治正确面前,作为女人,作为妻子也必须克制自己的委屈和不满。所以作为“荡妇”的慰安妇和作为“圣女”的后方妻子,实际都是日本社会“厌女症”对女性的压迫。
写到这里,我们大概可以明白“厌女”二字并非狭义上中文解读的“讨厌女性”,而是整个社会层面对女性因性别原因造成的压迫、歧视和偏见。
既然是全社会层面的“厌女症”,如果仅从男性角度进行批判似乎就带有天生的偏见,所以上野写到了女人之间的“厌女症”,尤其是在日本近代特色的女校文化中。这种性别单一学校的生存环境和性别混合制学校有很大的不同,在女校中学生内部将每个人按三种分数进行评分,即“女性分数”,“学业分数”,“被女人接受的分数”。对于这三种分数,上野的解释是,对于“女性分数”高的女生,周围原本没有期待她的学业,因为她已经拥有了美貌漂亮——被男性世界认可的资源。而对“女性资源”匮乏的学生,她们从小就被教育“像你这么难看的女孩,不好好学习还能怎么办?”反之,学业分数低的女生则试图以“女性分数”为替代资源,以此建立起对学业优秀女生的优越感。她们往往嘲讽那些成绩好,但“女性资源”相对匮乏的同学——“丑女”或者“不懂男人”之类的挖苦词汇。当然还有第三种,即“被女人接受的分数”,其拥有者大多数是具有领袖气质,略带“男人气”的女生,她们往往是班级里的话事担当者。但当这类人离开女校进入社会后,会因为性别环境的差异而对自己的身份产生迷惘,然后渐渐的,她们会懂得曾经被女人喜欢的女人,并不一定会获得男人们的认同。
所以,上野看到了近代日本女校中同性同学间的龃龉和群体间的角色划分,也是以男人的视角来评判的,即使在单一性别的女校,也逃离不了社会上“厌女症”的侵蚀。
同样,女生们为了在女校环境中更好的生存,某些“女性分数”高的女生会主动地披上“山姥的假皮”。所谓“山姥的假皮”就是在日本民间传说中,为避免灾祸,让美女变身为老妪的一种法术道具。而在女校环境中,“山姥的假皮”就是为避免来自同学间的羡慕嫉妒,主动丑化,谐星化自己,把自己当做众人的笑料,以牺牲“女性分数”来获得周围同学的好感。但进入社会,随着男性视角的引入,这样的主动扮丑就会消失,转而是同性之间更加激烈的“女性分数”的竞争。
那么从女校毕业进入社会的日本女性究竟面对的是怎样的社会伦理环境呢?通常认为日本社会进入近代化的标志是明治维新,但是在社会家庭和女性地位方面,日本的近代化演变却缓慢得多。所以长期以来,对于即将步入婚姻的年轻女性,她们被灌输的爱情观念是,“爱”就是勤快地照料男人的日常生活,一旦喜欢上一个男人,就到他的住出去,为他打扫屋子洗衣做饭。而对于日本妻子,夫妻生活是对丈夫的“奉献”,是不能说不的“任务”,不是近代资产阶级所宣扬的婚姻规范是“性快乐的权利与义务”。这是日本传统女性闻所未闻也未曾设想的观念。所以写到这里的时候,上野尖锐地指出“资产阶级社会似乎在日本从未成立过”。
我读到这里的时,对上野的结论惊得毛骨悚然,东亚文化皆受儒家影响,浸淫数千年,他们遇到的社会问题,我们同样也会遇到。所以尽管他们的政治,经济已经按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式运行,但文化方面似乎还有些脱节。而我们的妇女解放运动似乎更晚一些,尽管我们认为自己的社会模式比资本主义更加超前和先进,但在文化领域我们也跟上了吗?
而越过千禧年,进入现代社会,日本已早于我国遇上了人口问题。上野借用了日本作家酒井顺子在《少子》和《败犬的远吠》中的观点来说明日本社会在面对出生率和结婚率双双下降的环境中的女性问题。所谓“败犬”是指没结婚的女人的自嘲,当我们熟悉日本传统普通家庭构架中“没出息的父亲”,“不满的母亲”,“不成器的儿子”和“不开心的女儿”的角色设定,新一代的年轻女性希望能跳出这样的循环,拒绝由“不开心的女儿”变成“不满的母亲”。在面对传统势力针对婚姻和生孩子的拷问时,她们选择以“因为怕痛所以讨厌生孩子”这样的理由来应对,试图被世俗社会所理解。因为传统势力始终在给年轻女性灌输这样的观念——“无论怎样的疼痛,一旦看到孩子的脸庞,顿时就烟消云散”。而类似“我就是单纯的不需要,也不想生孩子”还是日本社会的“禁忌”。
少子化的问题还体现在那些无男孩的家庭中,在这样家庭中的女儿,尤其是长女,必须承担起儿子角色的重任,所以长女在日本民间又被称为“长着女人面孔的儿子”。本文开头提到的“东电女职员被杀事件”的受害者渡边泰子就是这样家庭中的长女,并且更为不幸的是,在她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整个家庭成员变成了她和母亲,妹妹三个女性。所以我们不得不推测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泰子还得承担起“父亲”的角色。介于案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进展,社会舆论纷纷猜测泰子是由于背负了家庭太多重任才导致精神世界崩塌,也有人认为职场中的男性霸凌现象是导火索,更有夸张的说法,认为她的是自堕地狱以拯救男人的“黑色玛利亚”,类似于我国民间传说中的“佛妓”。不过上野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认为这是典型的“男人的解释”。
“东电女职员被杀事件”在当时引起社会层面的广泛讨论,除了案件本身的离奇性外,泰子的身份反差也触动了很多日本女性,她们心里呐喊“东电女职员就是我!”。无独有偶,在2008年6月8日秋叶原发生了造成7死10伤的无差别杀人事件,案犯加藤智大是日本典型的“无人气男”,从小生活在父母的高压环境中,性格自卑而敏感。被捕后加藤声称他的作案动机是对生活感到苦闷和厌世。他在行凶当天在网络留下了“如果我有女朋友,性格也不会这样怪癖”的话。加藤智大这样缺乏女性接触的“无人气男”同样在当时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上野指出在“秋叶原无差别杀人事件”之前,一篇名为《想扇“丸山真男”的耳光——31岁、无业、愿望:战争》的奇文,其实就是这类事件的预警。文章中写道:
“我,作为一个三十一岁的日本男人,理应位于在日韩国人、女人、因经济景气好转而轻易就职的比我年轻的人们之上,理应得到比这些人更受尊敬的地位。即使没有正式职业,即使是无力的贫困劳动者阶层,如果社会转向右倾,那我也能恢复作为人的尊严。”
所以日本右翼传统势力和“厌女症”,在某些方面有高度的重合。在这样的思维下,女性被它化为某种能够印证男性社会地位的客体。上野引用了赛吉维克“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这一概念,用英文单词区别是“homosocial”和“homosexual”,即不存在性爱关系的男人之间的纽带,也可理解为是男权社会对同性的社会地位的认可。所以上野认为,类似加藤智大这类人,他们渴望女性的真正原因并不是“性”或者“爱”,而是他人对自己男性社会地位的认可。
后记
春节假日结束,我也终于怀着好奇心把这本让读者,尤其是男性读者不那么愉快的书读完,并写下了这篇读书笔记。全书主要是描述的日本,但东亚文化同宗,我很难不去联想到身边的林林总总。“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样的话,上古的圣贤们作为警示名言流传了上千年,上野所说的“厌女症”也同样浸入了我们社会的骨髓中。我并非女性/女权主义者,但在今日,我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政治、经济、科技方面的高速发展,社会和文化方面同样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去正视他们,正视多元化的社会,才能让历史的创伤愈合结痂。
大年初四我在一位摄影师朋友家,在欣赏他收集的一些山西古寺佛造像的图册,讨论对佛像修补上色的问题时,我突然想到了最近阅读的上野千鹤子的《厌女》一书。我们在历史上筑庙造神,在精神上诵读圣贤经籍,但时间一长,遭受岁月的侵蚀,曾经那些神圣得不可置疑的佛造像和经籍都会出现裂痕和伤口。为了让虔诚的信徒继续匍匐朝拜,我们只有不断地修复这些裂痕和伤口,让她结痂。
这两年,几路友人都推荐过让我去看看《厌女》,并期待书评。我当时的回应应该都是类似,“不看我也知道内容是在说什么,且大概率在获得新知和启发层面,我会觉得是浪费时间”。这阵子上野千鹤子又很火,我就又想起来了。昨夜睡前饮酒无事,也很快就看完了。就和之前我预料的差不多,觉得讨论的范畴和深度都很受限,仅是系统性地说了一堆现象,以及在局限的范畴下,对这些现象的 “定义级解释”,即本质上还是代表的是意志,却缺乏定义这些现象的是非优劣的动作,也没有深入分析这些现象的成因。(类似萨特或波伏娃等人的有关这些话题的书,我很久前也看过,感受也是类似,即 “我显然并不反对但也不觉得有现实支持意义的范畴受限的车轱辘话”,且在今日的范畴看来,既像是4090在看GeForce256,又像是在看螺丝壳里做道场)对这些现象的描述和定性,对我个人来说,既没有新意,也没有意义的。没有意义的原因之一在于,我在是非层面上本就有更复杂的质疑,之二是在个体志趣层面,我本也就不觉得的两性问题是个很重要的人类问题(相比国家矛盾、科技局限和阶级矛盾等话题来说),之三是我与作者类似,并无法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论,且我对问题可以按照我也认可的应然目标得到解决也并不抱有信心,且这里的不抱有信心,并非是对男人或女人没有信心,而是根本对人的理智就没有什么信心。于是最终的态度就只有,若一些女性(也可以包括一部分男性)在看过这些作品之后,产生了类似 “啊!就是这样”、“原来如此”,进而产生了一种 “我该这样想这样活” 的真实或幻象,然后在一段时间后,扪心自问,不自欺欺人,真的明显提升了主观福祉,那我都是绝对支持并乐见的。这就像是,一切并非是被上位者私利所定义出来的 “人类自由与解放”,不论定义我个人是否认同x,是否觉得在群体层面有意义,我也起码都是没有任何理由去唱反调的。但超过以上个体意义范畴的群体范畴,对这类话题,起码对这本书,我个人确实是不太以为然。而此处的不以为然,既不是反对,也不是贬损(只有相关领域的作者常见的在 “范畴” 层面的极度狭窄,我觉得是可被贬损的),而就是对人的可建构性的不以为然。只有深信人类的理智和高级的人,才会迷恋各种优劣的定性和应然的追求吧。但我确实不信这个,我觉得人类就是理性程度颇低的动物而已。这就像是,虽然我很确定我真心追求人的阶级平等,但同时又知道,这种就是一个程度的追求,且会时时刻刻被各路其实只是想阶级上位的人利用。绝对的阶级平等,哪怕是很高程度的阶级平等,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阶级性本就刻在我们的基因深处。这种追求,若被定义为应然,然后去建构,没问题。但只要建构过了头,不论是过去的实例,还是对未来的预测,大概率都是社会灾难,因为智人真的hold不住那种程度的逆本性。
引申话题就是,我多次说过,我并不希望我国未来成为今日帝国那样的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的剥削帝国,而是对世界人民大团结还留有理想的初心。但我又确实知道我们人类是什么一种德行,且其实我们已经活在了可以随时验证大过滤器可能的时代了,那么若结果依然是,我们到了老年时,或我们的子孙,可以历史周期地爽那么几代人,也不是不能接受,反正都一样,不如自己爽。两性也是类似。我坚信若有个大型实验装置(显然并不可能),把一堆智人男女完全隔绝外部社会建构地观测起来,最终的结果,必然还是会养出一群被定义为 “厌女” 的男人和女人来。而同样的设定,仅对这群智人男女按照女性主义的建构去进行社会性输入,结果也肯定不是一个更美好的两性小社会,而大概率会因为过度建构而走向某种人伦灾难。比如两个常见的现象,男性的互相定义和开除,女性的慕强和雌竞,我相信它们可以说是有文化性的,于是可以被建构所调整。但文化性终究是有强烈的生物性的(草履虫永远也不可能被建构出人类文化),于是这些可能过分了我也会鄙夷的两性特性,终究还是会存在,且两性中的大多数人,会在自发均衡态实现后,达到群体层面的福祉最大化(而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个体皆能最大化 — 并非不值得追求,而是不可能实现)。这又回到了我先前多次提到的那个断言:今日一切称得上 “好” 的广义社会学 / 人类学/ 政治学,将 “人” 从 “拥有理智” 的自我陶醉神坛上拉下来,起码部分接受我们就是 “聪明一些的无毛猴子” 的属性,皆为必要条件。而鉴于人伦和生产力绝对不允许我们在生物层面上重启进化,那么若一个人真的在社会学层面上有理想建构的兴趣和野心,Ta成为一个积极的技术党,就是唯一的逻辑可能了。
所谓文化,便如同强制性地加在我们身体与精神上的模型,去掉这个模型,就像不穿整形矫正服就不能走路的患者,或许身心皆会坍塌。
可是,模型毕竟只是模型。既在变化,也能改变。改变生活习惯并非易事,但认识到那不是宿命而只是习惯,总是好的。
——上野千鹤子《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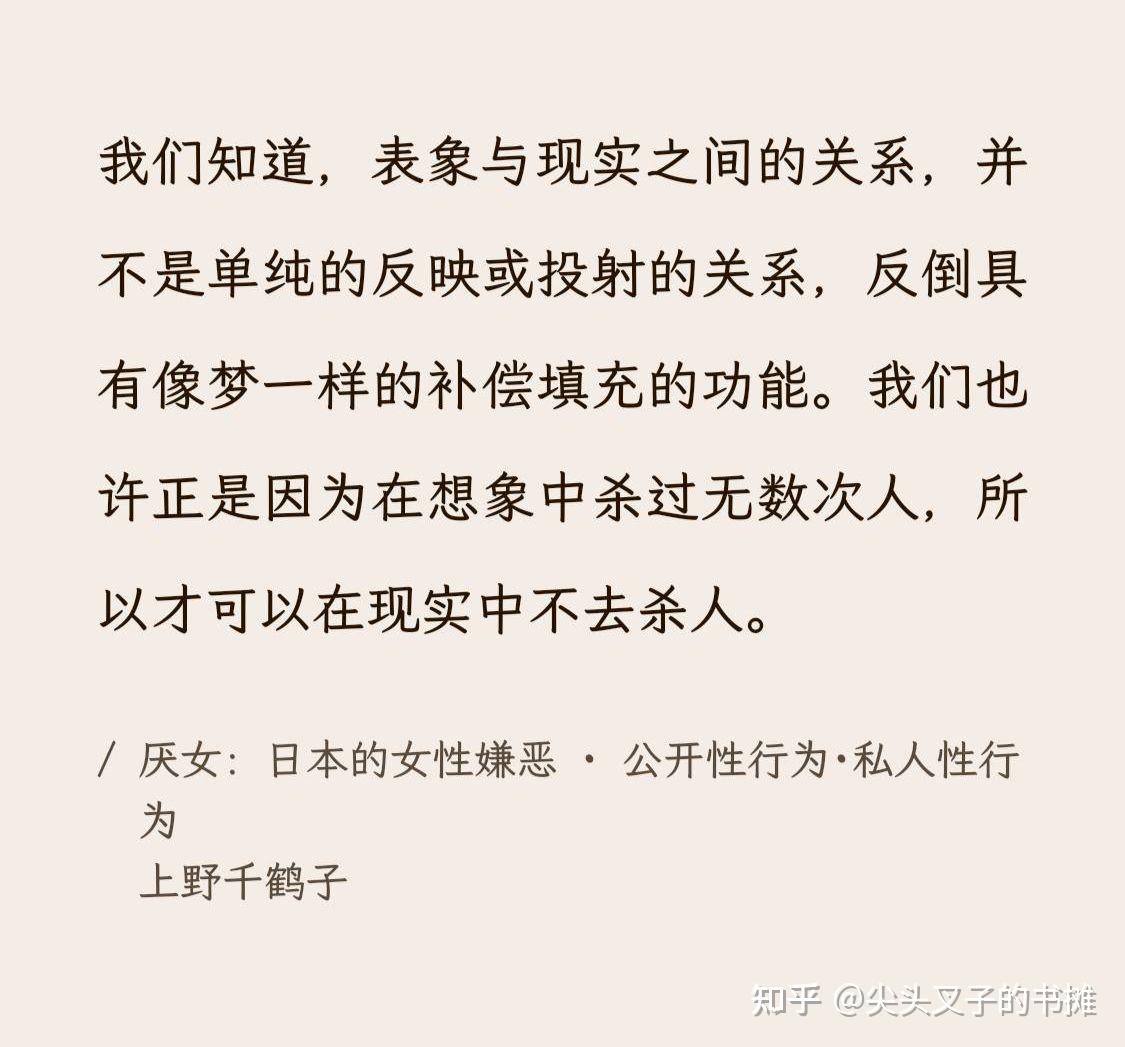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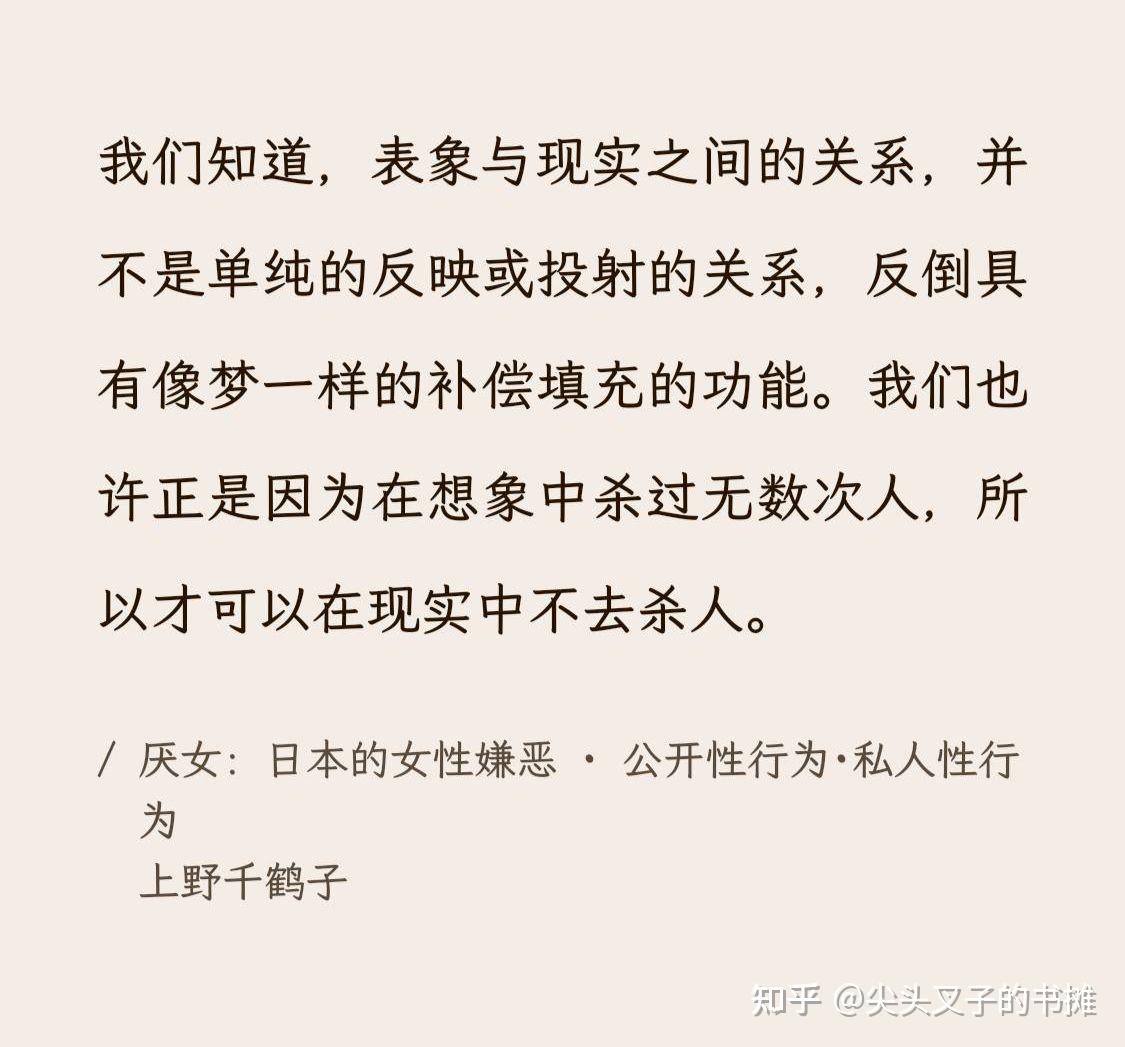
上一篇:读“外戚世家第十九 ”
下一篇:P连讨论串2022.4
最近更新科技资讯
- 22年过去了,《透明人》依然是尺度最大的科幻电影,没有之一
- 人类基因编辑技术及其伦理问题
- 不吹不黑,五阿哥版的《嫌疑人》能过及格线
- 论Lacan心理公众号的“双标”特质
- 猎罪图鉴:犯罪实录 女性伦理
- 清入关的第一位皇帝是谁,清朝入关后有几位皇帝?
- 描写露台的优美句子
- 谭德晶:论迎春悲剧的叙事艺术
- 中秋节的好词好句
- 《三夫》:一女侍三夫,尺度最大的华语片要来了
- 赛博朋克的未来,在这里
- 文件1091/721/2A:反概念武器实体的一封信件
- 尤战生:哥伦比亚大学点点滴滴
- 韩国最具独特魅力的男演员(安在旭主演的电视剧有哪些)
- 乃至造句
- 请保护好我们的医生,他们太难了
- GCLL06-土木工程的伦理问题-以湖南凤凰县沱江大桥大坍塌事故为例
- 黄金宝典:九年级道德与法治核心考点必背篇
- 【我心中的孔子】伟大的孔子 思想的泰山
- CAMKII-δ9拮抗剂及其用途
- 选粹 | 郑玉双:法教义学如何应对科技挑战?——以自动驾驶汽车为例
- 苍井空37岁宛若少女,携子送祝福遭热讽,下架所有视频母爱无私
- 日韩新加坡怎么对待影视剧中的裸露镜头
- 中西方文化中的颜色词
- 土豪家的美女摸乳师——关于电影《美人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