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机访问:wap.265xx.com
手机访问:wap.265xx.com如何评价《万历十五年》?
也许,以今天的视角和学术史的意义来看,黄仁宇的判断充满了不少以己度人和后见之明。但是依旧有不可取代的价值,他深沉的历史感和对于官僚体制和结构的深刻洞察也许在今天仍未过时。
中国为何无法成功地回应西方冲击?
《万历十五年》中文版的作者简介告诉我们:黄仁宇,1918 年生于湖南,天津南开大学肄业。他大学没有念完。依照正常的学程,应该 22 岁从大学毕业,算一下,他 22 岁那年是 1940 年,那是抗战时期。所以他离开了南开大学,进了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因为进入了抗战后期,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中国和美国并肩作战,他得以有机会到美国。他得到的正式学位,一个是“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毕业”,另一个则是“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博士”。
他可不是正常进大学得到学士学位,再进修硕士,然后进博士班,最后取得博士学位。在这中间有“历任国军排长、连长、参谋等各级军官”,然后是“随国民政府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将军解职退伍”。退伍之后,他才得以在美国攻读研究生,才最终得到密歇根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学位。他成长于中国最动荡的时期。1918 年是“五四运动”的前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三年。用殷海光(1919 年出生)的话 形容,他们这一代是“后五四人物”,没有赶上“五四”的光辉风华,却深受“五四”所创造的新文化最强烈的影响、模塑。“后五四人物”的青春时光没有办法用在文化创造上,而是经历了战争的磨难,而且黄仁宇还是在第一线上以军人身份见证了战争,大学没有毕业就应召从军,再进了军官学校。以军人身份去美国受训,他得以和“五四”的文化知识背景接轨,接触到西方的知识与生活。
战争与军事生涯拖迟了黄仁宇的学术文化追求。他到 1968 年才在美国找到教职,再算一下,那年他已经 50 岁了。他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他的老师是当时任教于密歇根大学的余英时,而余英时出生于 1931 年,比黄仁宇小 13 岁!黄仁宇是不折不扣的老博士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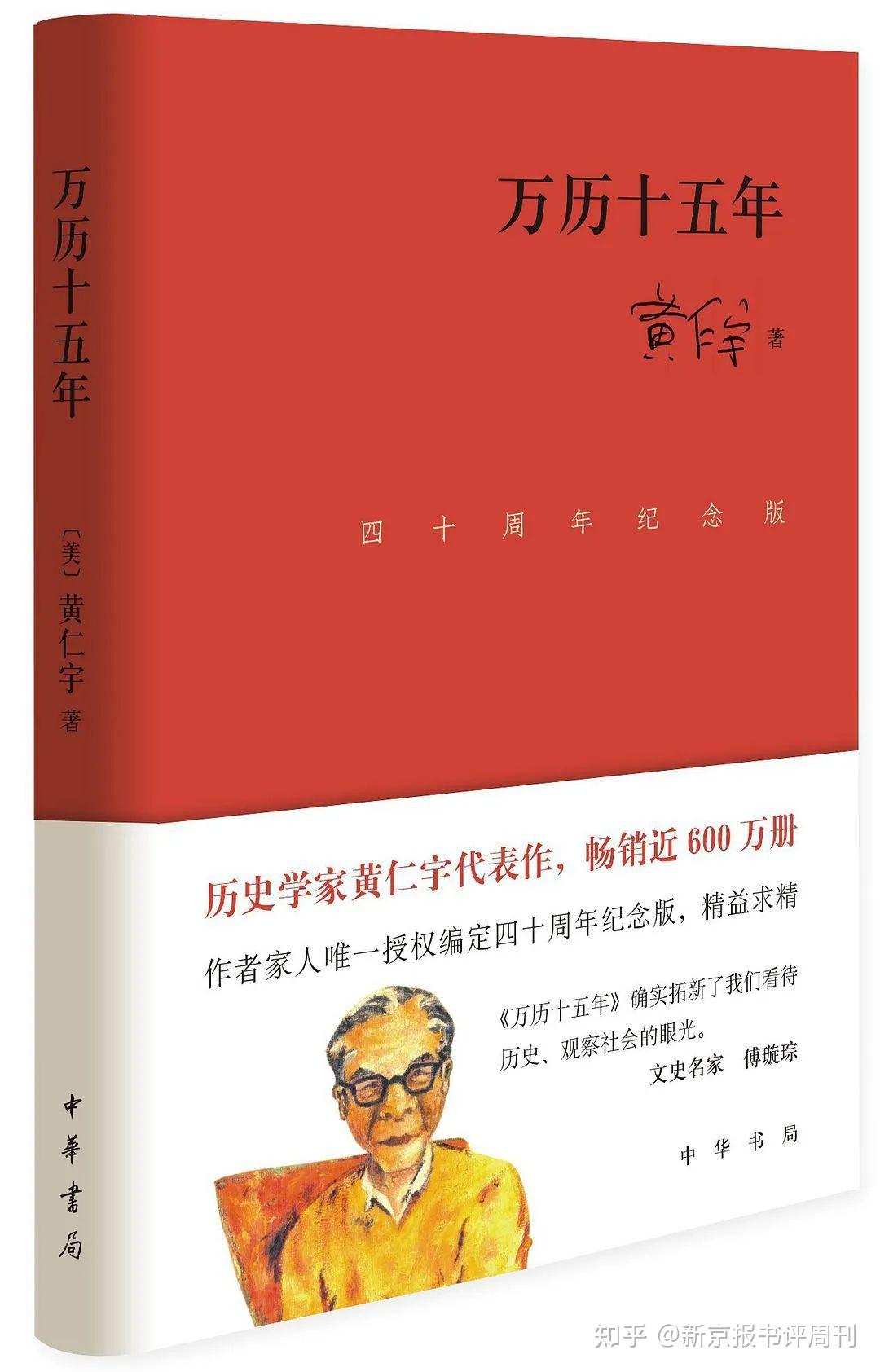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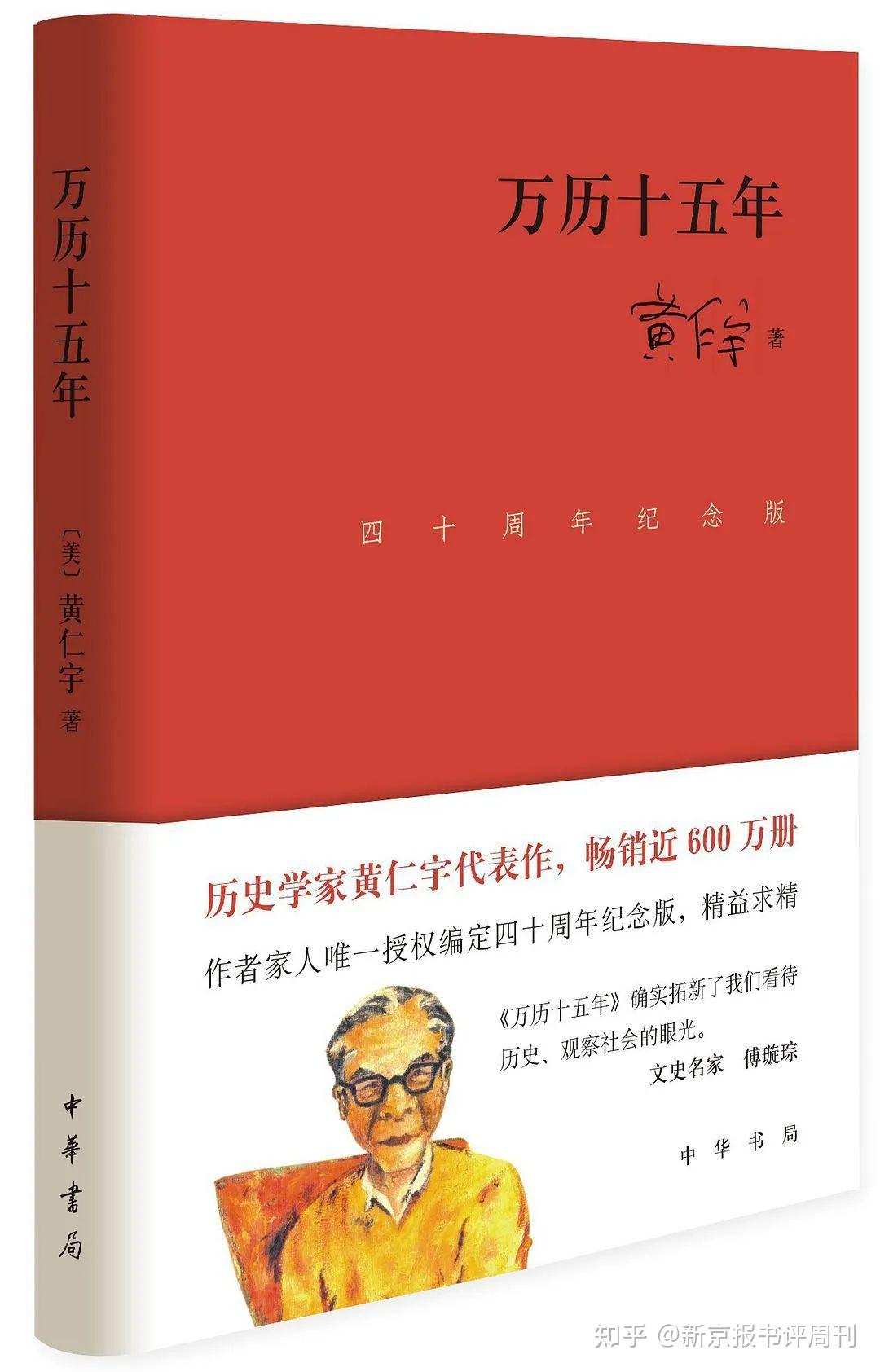 《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 版本:中华书局 2022年4月
《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 版本:中华书局 2022年4月
可以这样说,黄仁宇的前半生,被时代和国家耽误了。他的经历用传统说法来说是“折节读书”,放下军旅的成就,中年以后重新安静下来做学问。所以不只有一种正常读书人不会有的知识饥渴,而且他特殊的生命经历必定会影响他如何看待历史,如何研究历史。
他念兹在兹的是:为什么中国如此悲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时代,眼前看来都是不成功的改革、一连串革命的挫折?他出生时,辛亥革命已经成功7年了,然而他却从来没有享受过革命成功带来的好处。
革命为什么无法完成?在书序中,黄仁宇就是要告诉我们,这是他心中的根本大问题,他之所以研究历史,是为了认真追求这个大问题的答案。很多人困惑于这个问题,不过一般的答案都局限于个人有限的生命时间尺度,找出了袁世凯很可恶、军阀恶搞割据、蒋介石不抗日、汪精卫卖国等原因。
但黄仁宇察觉到革命的来龙去脉,和我们个人的生命不是同样的时间尺度,用个人的时间尺度,倾向从现实里去找答案,可是如果要用不同的尺度,那就必须往历史中去探找。向后推,很容易就看到鸦片战争,看到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影响。
黄仁宇在美国也和费正清上过课,很熟悉当时最流行的 “西方冲击,中国反应”观点。1840 年之后,中国历史最主要的现象是西方势力带来了一波波前所未有的挑战,刺激中国不得不摸索做出各种反应,革命是其中一种反应。于是革命的失败也和之前的其他反应,例如自强运动、变法维新一样,都是这套传统无法应对西方挑战的结果。
不过显然黄仁宇的疑问无法停止于这样的解答上。他认真再往前追溯:那为什么在西方冲击来到中国时,中国无法成功地响应,因而酿造了黄仁宇他们这一代人必须亲身忍受的种种痛苦?其中一项具体的痛苦,是和日本人打仗。
黄仁宇是一个曾经冷静地和日本人打过仗的中国人。他那一代有过战争经验的中国人,其中一种终生仇恨日本,激动得不想再和日本有任何关系;另外一种则虽然也终生仇恨日本,却念兹在兹思考日本,在他们脑中不断盘桓一个疑问:为什么同样遭受西方来的狂风暴雨般冲击,日本的回应远比中国好得多,成功得多,以至于最后甚至以中国作为他们成功响应西方强大升起后的踏脚石?
显然黄仁宇属于后面这种人。比较中国和日本,他更明确要问:为什么中国颠颠踬踬走了很久走不出来的这条革命长隧道,日本却走出来了?《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序中他说: 我们小时候读书,总以为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在短时间把一 切弄得头头是道。殊不知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其社会已在 步商业化。况且明治维新进步过猛,其内部不健全的地方仍然要 经过炮火的洗礼,于世界第二次大战后,忍痛改造。
这么简单的一段话,表达了黄仁宇的态度。经过和日本历史的比对,他认识到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必须更进一步往上追溯,去看西方冲击来到之前的中国社会,看是什么样的因素,使得中国无法有效地应对西方的冲击,而在西方冲击中一蹶不振。
他不断认真地往前找,最终找到的答案是:如果我们能够好好地看清楚并解释 1587 年,16 世纪末的中国,就不会意外后来中国会如此难以适应新挑战,会迟迟无法推动新改革。
集中在一个特定尺度上的“大历史”
黄仁宇提出“大历史”的观念,和“小历史”对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重点在于“作者及读者不斤斤计较书中人物短时片面的 贤愚得失”。这话有两方面的意思。
一方面是告诉我们,《万历十五年》书中讲到明神宗、申时行、 戚继光、李贽、张居正,不是为了要从当时的情况去讨论他们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这里做对了、谁那里做错了。而是从一个更长远的“大历史”角度去看,他们代表了什么。另一方面,他也要摆脱从现实、狭窄的角度来看现代史,来解释中国革命的成败 得失。
这篇序文写成于 1985 年,离黄仁宇去世只有十几年时间。在那十几年中,他反复不断以各种方式,运用各种史料来讨论“大历史”。他从西方近代历史变化角度写了《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从中国通史角度写了《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黄仁宇提出的“大历史”观念,和法国“年鉴学派”的主张看 起来有相似之处,但根本上不一样。“年鉴学派”建构的历史比较 接近完全历史:历史有各种不同的变化速度,要用不同的时间尺度来衡量、来看待,依照时间尺度来观察、记录各种不同节奏快慢的变化。将这些不同节奏快慢的变化放在一起,才能够将历史的许 多环节解释清楚。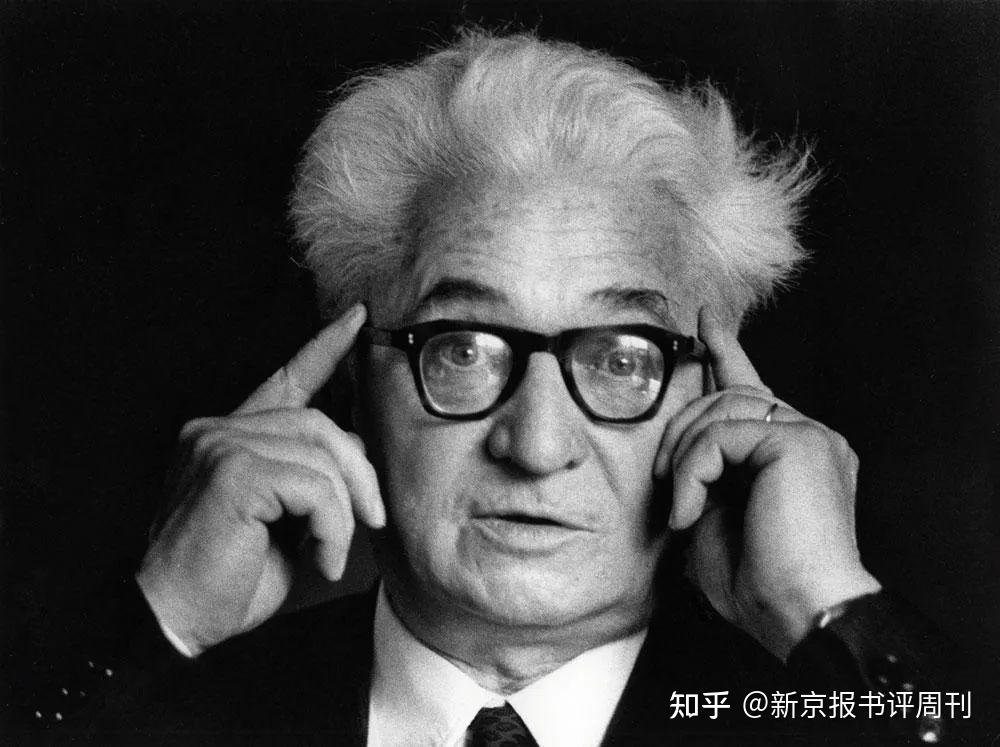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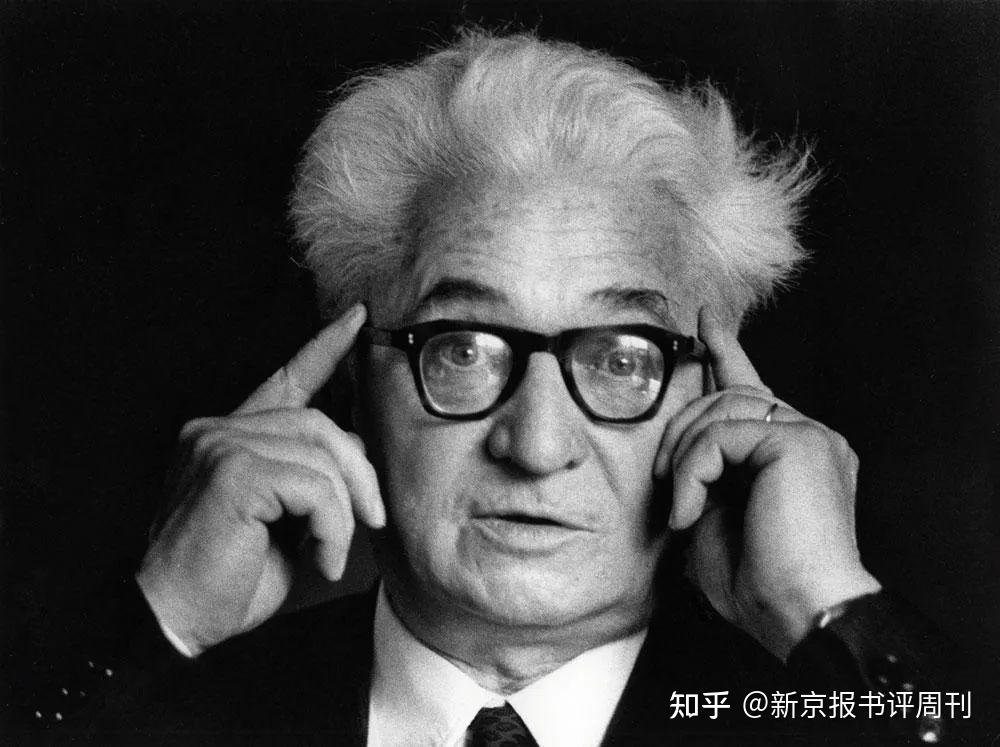 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
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
例如说地理,看起来完全不动的因素,却必然影响甚至决定一个国家的军事发展策略与条件优劣。“年鉴学派”也强调不能忽视变化较慢的部分,但相较之下,黄仁宇更重视一种人际互动模式所 构成的社会结构,对于比这个变化更慢的地理、农业、城乡动线等等,他就没有那么在意。也就是他的“大历史”集中在一个特定的尺度上,和“年鉴学派”整合各种尺度的野心仍然区别明显。
黄仁宇是抱持着现代中国“革命史观”问题意识去研究明朝历史的。他不是要看明朝本身发生的事,而是要探讨明朝所形成的 社会结构。了解他的这份根本、深厚用心,我们更能体会到黄仁宇了不起的历史写作技巧。
一般的历史研究者、讲述者,当要说明中国社会结构时,一 定会动用一套结构性的语言。“皇权”“相权”“儒生”“官僚体 制”“商人阶层”……用这种抽象、集体性的语汇来描述、解释社 会结构。谈结构,就像盖房子一样,将房子先分出地基、梁、柱、 墙、屋顶等等,才能讨论这些部分的彼此关系如何形成。
黄仁宇的思考方式却是:所谓结构,就是潜藏在表面变化之下,却比表面变化更根本更重要,甚至决定、左右了表面变化的各 种因素、各种力量。那么换相反方向看,真正有决定性作用的结构,就应该和表面的变化有着清楚的联结。也就是如果结构是基本,而且真的那么基本的话,那么摘取表面的现象,即便是微小的现象,都应该能够联系到底下的结构因素。如果表面现象联系不到底层结构,那岂不就表示那结构不够根本,不是真正根本吗?
于是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历史上挑出一年,整理这一年 中发生的各种现象,然后用这些现象回推去认识、去展现那段历史 的结构性决定因素。这是高度原创的论理形式,而黄仁宇还用同 样具备高度原创性的叙事文字来表现论理上的创意。
1587 年 —无关紧要、没有大事发生的一年?
《万历十五年》先以英文写成,在美国由耶鲁大学出版,书名是 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由大学出版社印行,表明 了这本书的学术性质,出版之后,前八年这本书都没有印平装本。这在学术书领域中很常见,因为针对的是图书馆或专业读者,想读、要买的人不会为了售价而改变心意,出版社当然不需要以平装低价来扩充销量,维持精装高价可以有较高的收入。
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而且既非通论性质,也非关系时事现实议题,是讲绝大部分美国人都没听过的明朝,可想而知就算出较为低 价的平装版,也不会吸引多少读者。
然而黄仁宇这本书创下了耶鲁大学出版部精装本学术书的畅销纪录,卖出了十几万本,成绩比很多平装本图书都要好。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值得注意、需要解释。为什么那么畅销?而明明畅销了,为什么出版社却不出平装本?
因为出版社准确判断出会买这本书的人,不仅仅是因为对中国历史有研究、有兴趣,他们基本上因为口碑推荐而来,主要是对于书名中显示的历史研究法、历史写法感到新鲜好奇。也就是说这是一群有相当人文知识专业训练的读者,他们很清楚自己要从这本 书中读到什么、得到什么,也就有很强烈的动机愿意多付一点钱买精装本。
书名中最诱人的是“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这在中文版中不见了。无关紧要的一年,没有大事发生的一年。一本历史书,选择只讲一年的历史,已经不寻常了,更奇怪的是,竟然还刻意选了一个不重要的年份。
这明显违背了历史学的常识,甚至违背了更普遍的记录原则。小时候老师教你开始写日记,一定告诫你:不要写洗脸刷牙、吃饭睡觉。那是日常,那是平常,日记要写今天和别天不一样、特别发生了的事,或特别的感想。
历史记录也就是从这样的原则扩大而来,有事则长、无事则短,记录之先一定要判断重要不重要。但黄仁宇写的历史书却是摆明选了不重要的一年来写。这是很巧妙、很有效的策略,立刻吸引了这类书籍读者的注意,而且也理所当然为读这本书的人提供了对其他人介绍以及和别人讨论本书的重点。
这本书的内容并不是真的只限于 1587 这一年,但如此定书名 表现出很不一样的历史态度与历史学方法。选无关紧要的一年,意味着不被表面的“大事件”所眩惑,我们得以看到一个时代、一 个社会的结构组成。
“大事件”之所以是眩惑,因为其中牵涉到许多偶然因素,描述“大事件”要花很多工夫、篇幅在这些偶然因素上,更因为偶然的介入,很难对“大事件”给出完整的解释。从叙述到解释,一 定会有“恰好”“不巧”“没想到”“偏偏是”这一类的字词标示了解释之困穷。
没有大事,才能从表面的正常、平静中,看出一个时代的政治、社会、经济运作规则。这样的时刻,不会真的什么事都没发生,于是还可以换一个角度看到,一些从“小历史”角度不被重视的事,如果换了“大历史”眼光之后,其实影响甚大。如此又将 “No Significance”—无关紧要,变成了吊诡、不确定的形容, 是从什么样的历史研究与理解角度判断为无关紧要的呢?
不看人物的短时片面,看更根本的结构
1588 年 1 月,但以农历计算还在前一年的十二月,一代名将戚继光去世了。依照黄仁宇的评断,戚继光最重要的历史地位,建立在为明朝打造了一种特殊的军事组织,之前没有出现过,之后也无法再造。
也无法再造。黄仁宇在书中解释得很清楚,那是因为戚继光的军队,不是中 国传统社会结构所能承担的。戚继光去世时,没有人能看见,那 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而且是中国唯一的一次军事改革实验到此落幕 了。也是要到后来,有了宽广的历史眼光,才会看出来历史的巧 合竟然衔接得那么紧密。同一时期在欧洲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是 英国海军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将世界历史带进了新的海权时 代,而中国刚刚错失了可能参与的关键条件。
又例如在 1587 年当时看起来的一件小事,一件 No Significance (无关紧要)的事,在东北边境的建州卫有一个部落的领袖逞其武勇,攻打周围的邻人,消息传到朝廷,大臣分成两派争议到底该剿 还是该抚。一度要剿的主张占了上风,但派去的军队却被打败了, 于是转而变成要抚的主张被采纳了,实质上就是恃其距离遥远,不理不管算了。
那个武勇的部落领袖,叫努尔哈赤,他的名字在 1587 年第一 次出现在明朝的记录中。
努尔哈赤的行为,以及明朝朝臣讨论与决策到执行并转向的过程,有哪些是偶然的?又有哪些反映了结构性、近乎必然的现象或问题?回头看历史,从后见之明,我们常常扼腕,当时怎么会如此轻忽,怎么会就这样放过了可以节制、压抑后金崛起的大好机会呢?
千金难买早知道,而我们却总爱用“早知道”来看待及评论历 史,这就是黄仁宇所说的“斤斤计较书中人物短时片面的贤愚得失”的态度。
黄仁宇在书中试图让我们看到,这不是少数几个人的错误判断,而是:首先,当时明朝的军事组织与军事运作,没有条件可以出关打努尔哈赤。其次,要建立足够的军事力量出关压制努尔哈赤,明朝需要完成如同戚继光所从事的改革,但戚继光的遭遇却已经证明了这样的改革无法彻底,也不可能复制。派戚继光去打努 尔哈赤也不可能胜利。
那不是戚继光的能力问题,不是这些大臣的判断是否正确,而是由更根本也更庞大难以改变的结构所决定的。
什么是结构?例如说国家财政是结构的重要一环,黄仁宇撰写《万历十五年》之前,他所出版的著作,从他的博士论文扩充改写的,就是探讨 16 世纪中国的财政状况。书中清楚列出了那套制度的错杂夹缠问题。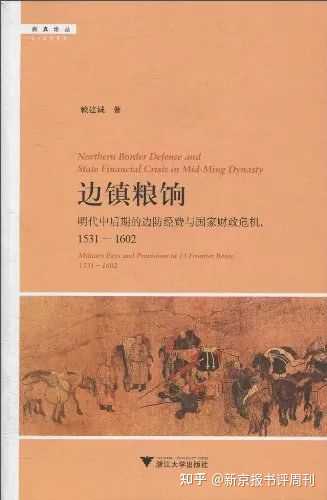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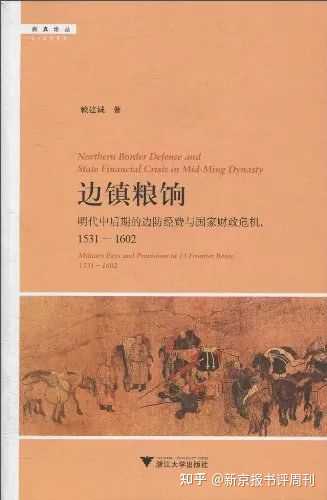 《边镇粮饷》作者:赖建诚 版本:启真馆·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年8月
《边镇粮饷》作者:赖建诚 版本:启真馆·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年8月
现代国家的财政基础,都是总入总出的原则。国家的各种收入,每个人每个公司所缴的各种税,都进入国库,然后由国库去支付所需的各种公共花费。如此才能有预算与结算,预算和结算都必定是分成“收入”总项和“支出”总项的,也才能算出收支是否平衡,盈余多少或短绌多少。
明朝的财政不是这样总体安排的。军费归地方政府负担,而由中央朝廷负责规划。如果在蓟州有两万士兵,朝廷命令河北、 山东负责张罗他们的所需。但如果这时河北、山东遇到干旱,他们需要救济,他们也向朝廷要钱。意思是各个不同项目分别处理, 没有统收统支,也就无法在各项目间合理、有效地调节。不断有 新的项目产生,每一个项目都产生新的行政程序,到后来必定是无论中央或地方都算不清自己的财务状况,等于是大家都只能见树而没有人能够见林,不只是没有人能掌握国家的总体财政状况,就连地方单位的账也都是一团混乱。
原本河北、山东用兵筹了军费,如果战事转到山西,山西苦哈哈筹不出军费,这时却无法将河北、山东省下来的军费拨给山西使用,于是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因为山西军费短缺,而使得转往山西的 战斗由胜而败,然后再来追究山西战败的人事责任。当时的政治体系用这种方式追究责任,后世读历史的人很容易跟着如此“斤斤 计较书中人物短时片面的贤愚得失”,这就是黄仁宇试图要避免的 一种态度。
本文经授权摘编自《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11》。原文作者:杨照;编辑:朱天元;导语校对:付春愔。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上一篇:公认最好看古装电视剧推荐,古装剧2022排行榜前五名
下一篇:当前热议!关咏荷第一任老公是谁?关咏荷为何选择与张家辉结婚
最近更新小说资讯
- 特别推荐 收藏共读|朱永新:新教育实验二十年:回顾、总结与展望(上)
- 网红+直播营销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 火星探测、卫星搜寻、星球大战,你有怎样的“天问”?
- 希腊男性雕塑 希腊人的美学,那里越小越好
- 枸杞吃多了会怎么样 成年人一天可以吃多少
- “妈妈和哥哥被枪杀后,我变成地球最后一个幸存者”:热搜这一幕看哭了……
- 节约粮食倡议书400字作文
- 祖孙三代迎娶同一个妻子,本以为是笑话,没想到却是真实故事
- 进击的中东,唯有一声叹息
- 唐山性感老板娘不雅视频曝光,少妇贪心,少男痴情!注定两败俱伤
- 【盘点】5G时代下,相关专业有哪些?
- 毁三观的旧案, 双胞胎兄弟交换身份与女友发生关系, 终酿伦理纠纷
- 腾格尔在当今乐坛的地位如何(腾格尔为什么能)
- 小贝日本游,11岁小七身材发育成熟,穿紧身衣有曲线,瘦了一大圈
- 甩三大男神前任,恋上有家室老男人拿下影后,她人生比电影还精彩
- 女英雄为国为民,先后嫁给3人,却落个精神崩溃服毒自尽
- 墨西哥超大尺度神剧,四对超高颜值情侣一言不合竟开启“换妻游戏”?
- 妈妈对小学孩子的成长寄语
- 面向未来的工程伦理教育
- 用大宝贝帮妈妈通下水道好吗
- 第36章:家庭伦理
-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考研看这一篇就够了
- 李玉《红颜》 电影带来的世界44
- 微改造 精提升⑩ | “渔民画云码头”,探索传统非遗产业化发展新路径
- 清朝皇帝列表及简介 清朝历代皇帝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