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机访问:wap.265xx.com
手机访问:wap.265xx.com解构主义是什么?学习解构主义对阅读文学作品有什么帮助?
文学理论 解构主义 文学作品
谢邀。
解构主义是一个“反结构主义”的哲学思潮,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由德里达提出(这里有朋友指出拉康比德里达早,特别补充上),不过我在这里主要普及下德里达好了,他的三部著作《语音与现象》、《论文字学》、《文字与差异》确立为解构主义的标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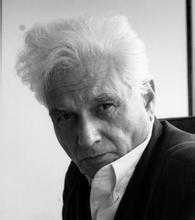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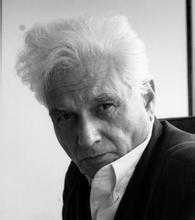
Jacques Derrida
“解构”源于《存在与时间》中的“deconstruction”一词,由钱钟书翻译,指每一次解构都对结构产生分裂和分解,但是解构的结果是又产生新的结构。
解构主义的特点是反传统,反权威,反理性,是对西方历来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反叛。
思想的源头是尼采和海德格尔。
影响范围涉及多个领域,有建筑、文学、艺术等。解构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后结构主义”,也可看作是结构主义的另一种形式的延伸。联系题主问题的后半段,可以确定您说的是文学领域的解构主义。
在文学领域,“解构主义”实践运用的代表是耶鲁学派。(代表:保尔·德·曼、哈罗德·布鲁姆、杰夫里·哈特曼和希利斯·米勒)但是耶鲁学派的一些教授并不承认自己等于“美国的解构主义”。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解构主义是哲学根源,文学实践上的代表是耶鲁学派。
那么题主可以去查询下耶鲁学派的相关文学理论,如布鲁姆的“影响即误读”;保尔·德·曼的修辞学阅读理论、米勒的“重复”理论等等。
至于“学习解构主义对阅读文学作品有什么帮助?”,我想和学习其他的文学理论一样,都是为了更好地阐述经典,挖掘文本的内涵,延续经典的生命力。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并不是反结构主义,而是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的一种。德里达(Derrida)是Deconstruction的创始人,其核心观点是对二元对立思维的一种质疑。德里达认为二元对立的两个符号(如内在和外在)中,一个符号包含了另一个符号的“印迹”(trace)——没有“内在”这个概念就没有“外在”这个概念,没有“外在”这个概念就没有“内在”这个概念。所以,“内在”这个概念中包含了“外在”这个概念的印迹,说明“内在”这个概念并没有一个独立存在的、本质性的意义,它只有与“外在”这个概念相对考虑时才可以被定义。一切人类语言和思维全都是基于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之上建立起来的。一切意义、一切符号都是通过延异(Différance)得到定义的。
延异(Différance):这个德里达发明的词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差异(Difference,正常的拼法)——语言和思维对现实世界进行的分类、区分都是通过不同概念之间的差异进行的,没有任何概念拥有内在的、独立的现实。第二层含义是延迟(Deferral)——每一个概念都是通过延迟对它的定义而产生的。比如说,如果你去查字典,每一个词都是通过其他词来定义的。如果你去查一个词的定义中的词,那个词也是通过别的词来定义的。这样的话没有一个概念拥有一个独立的、自成一体的定义。对所有概念的定义都是无限延迟的。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是对西方哲学传统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的挑战,与印度大乘佛教中观部的观点很像,对现实和语言都持有一种关系性的、非本质性的认知。
推荐看德里达的《论文字学》和《书写与差异》。如果英文好,建议看Arthur Bradley 的 Derrida's Of Grammatology,是一本非常清晰的解释。
很有意义的问题,聊聊我个人的观点。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这个问题涉及到阅读的一些根本的东西,如果能够深入研讨这个问题,对我们阅读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首先可以问这些问题:文本有答案吗?如果有,那是什么?如果没有,我们阅读的意义何在?
根据艾布拉姆斯的观点,阅读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而应该看成动态的,作者、文本、读者、世界在这其中不断角力,富于变化。
所以文本可能是有参考答案的,这个参考答案可能包括:
作品所反映的社会、主题。(以世界为中心)
作者写作时的所思所想所感。(以作者为中心)
文本的形式和结构。(以文本为中心)比如俄罗斯文艺家普洛普曾对100个俄罗斯故事进行细致的比较分析,找到民间传说的结构要素及其组合规律。英国文学评论家E·M·福斯特曾在经典文论《小说面面观》中将人物区分为扁形人物和圆形人物,并据此概括出了小说创作的一些原则,比如扁形人物被塑造成戏剧性角色的时候最为出色。
读者的“期待视野”。(以读者为中心)它是读者的全部文学记忆、隐含着过去全部历史。对于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读者,他们的“期待视野”都不是无限的,都存有历史赋予的基本标准。换句话说,在读者进入文本之前,已经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预知这位读者可能读到什么程度了。
当然,这些答案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着,但总体上来说还是处于稳态变化。
下面我们来聊聊解构主义。
解构一段话语,即是通过在文本中识认出产生了据说是论点、中心概念或前提的修辞活动,来表明话语如何损害了它所维护的哲学,或为它奠定基础的诸等级对立命题。解构的历史由来已久,解构是将事物内在逻辑推至极限,最终导致了其本身的分崩离析。
因此,解构主义并无更好的真理观,它是种阅读和写作的实践,与说明真理的努力中产生的困惑交相呼应。它并不提供一个新的哲学框架或解决办法,而是带着一点它希望能有策略意义的敏捷,在一个总体结构的各个无从综合的契机间来回流转。它在哲学的认真性中走进走出,在哲学阐说中走进走出。它虽然在一个松散芜杂的构架的内部和周围耕耘,而不在一块新的地基上建构营筑。
即:解构它并没有生成出一个更稳定的答案,它是一种极为强烈的质疑精神,一种主义,一种过程,是一种对既有答案和体系的挑战。它抓住已有逻辑的漏洞反复攻击(通过语词),进而期望揭开被权力层层困扰的语词本身,从而冷静地审视周围事物,不被意识形态所蛊惑。
比如诗经“后妃之德”的阐释就颇为偏颇,经不起解构的推敲。而通过解构,我们可以逼近更为真实的存在。
那么,什么是更为真实的呢?解构主义并没有给我们明确的答案,这也是众人质疑德里达的地方:你摧毁了原有答案,却不给我们新的答案。当然德里达或许会认为这种过程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它可以训练我们的质疑精神。诸如福柯对“性”这个语词的考证;阿多诺忧心忡忡地看到了被文化工业支配的资本主义文化;阿尔都塞干脆直言意识形态无处不在;德里达则尝试颠覆语词的权利结构,赋予女性(woman)、误读反抗男性(man)和阅读的一线生机。比如我们读到古代称赞一个女性守节,或者把女性赞美为天使的时候,我们可以质疑这种逻辑,是否将女性当作一个正常人来看待。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如果用好解构主义呢?窃以为或许要做到几点:
1、 解构是为了更好地建构。
霍克海默认为批判理论应该具有批判性,这一点还是比较同意,即应该创造出更好的局面。对于生活而言,解构是为了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自己,认识社会,比如“性“”法律“、“爱国“、”家务“、“婚姻”等词;偶尔反思一下,或许会有更为清醒地认知。毕竟人活一辈子,如果最后发现自己是为了一个毫无意义地目的活着,或者被欺骗、蒙蔽,也是一件挺悲伤的事情吧。
2、 解构主义应该和现象学批评、细读、外部批评等一起,构筑我们阅读的强大基石和内推力。
阅读文学是很痛苦的也是很幸福的,痛苦就在于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像理科那样找到一个完美的、确定的结构。这有点像康德的理论,我们永远无法了解物自体,得到文学的大一统框架。因为文学一旦确定了,有了统一的标准,几乎也是它宣告死亡之时。所以我们必须像西西弗斯那样一步步地咬牙向前,不断地阅读,总结,又不断地否定、超越自我。这也是阅读、审美的乐趣所在。
我个人还是比较认同现象学批评的观点的:一部经典作品是一个完美的圆,一部经典作品有一个“正典”式的解读和答案,现象学式文本解读就是还原和追求这种答案,假设这种东西真的存在的话。
解构主义、外部研究、细读确实可以让我们逼近这种本真的存在,我们在反复地质疑中推进着对文本的深层理解,这是一种阅读能力和审美能力的体现。
3、 不必每次都动用解构主义。
如果每次阅读,每个语词都用来解构的话,那就是另一种陷阱,另一种“刻奇”了。这样阅读、活着也会很累。
推荐书籍:
《文学理论入门》卡勒
《论解构》解构的经典入门书籍,但是还是建议先看看文学理论类的书籍。如果不是专业要求不必强迫自己阅读,还是有一定难度。
《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伊格尔顿写得极为传神的一部著作,值得一读。当然,不必强求。
窃以为,普通读者能读通这三本已经足够了。
菜单(有用的):杨韬: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
里面有对解构主义定义和发展历程的浅薄探讨;杨韬:卧虎藏龙:东西方的双重注视与反抗精神
有一定的解构主义实践在里面,质疑了原有逻辑,同时进行了建构;杨韬:充满权力与刻奇的语词:“家务”
进行了解构的生活实践。杨韬:博尔赫斯 《镜子与面具》批注阅读
一种高强度的阅读,对文本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现象学还原。当然你可以继续解构我生成的逻辑,这就是阅读的乐趣:不断建构,又不断超越。
感谢阅读,祝好运~
谢邀:
这个问题看起来很高深很专业,回答也看似不明觉厉,但仔细阅读起来,还是很轻松的,希望我的回答能给您带来帮助。
2007年7月,时当贝瑞·邦兹逼近全美棒球协会全垒打纪录之际,《纽约时报》体育栏目报道说:“邦兹在芝加哥的闲暇时光跟杰西·杰克逊一起祷告来着,拜访了其家人,解构了他的挥杆录像带。”
从《纽约时报》这段报道的表述中,人们发现了一个崭新的词汇——“解构”。很显然,“解构”已经进入语言,成为“分析”的同义词。但凡言及机制、程序和惯习时都是如此,虽然它的含义似乎尚未落定。
当代美国著名导演伍迪·艾伦在1997年8月27日于威尼斯电影节上映的影片《Deconstructing Harry》(直译《解构哈利》,豆瓣译名《解构爱情狂 》中,伍迪·艾伦宣称意在消解或清除围绕着哈利的不祥之兆,可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却暗示,邦兹的解构分析是给他的挥杆提供洞见,使他得以“消除若干瑕疵”。

“解构”这个词的奇崛命运,无疑是乔纳森·卡勒于1982年写成的《论解构》一书在尝试解释解构、审度它的文学批评内涵时至今日依然供不应求的缘由之一。
乔纳森·卡勒,是美国著名学者、理论家,著作等身,力作《论解构》问世以来便大放异彩,成为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的经典之作。在欧陆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被引入美国学界,并迅速获得普及的过程中,乔纳森·卡勒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传道人之一。他的学术巨著《结构主义诗学》和《论解构》,对欧陆结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作了准确地梳理和解释。
自乔纳森·卡勒《论解构》问世以来,在过去的近40年的时间里,“解构”这个术语是批评和文化论争中的闪光点之一,它是滥用的大本营和代名词,命名了种种困难,深刻影响了理论文字,同时也是20世纪思想中一个更广泛运动的名称。在这个世纪的思想里,一千年来哲学、文学以及批评传统中的种种假设和推测变得形迹可疑了。简言之,解构源出哲学家雅克·德里达著作的哲学与文学分析模式,它质疑基本的哲学范畴或概念。但是,解构从来就不是一目了然的。
 美国结构主义大师乔纳森·卡勒
美国结构主义大师乔纳森·卡勒
法国哲学家、20世纪下半期最重要的法国思想家之一、西方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雅克·德里达坚持说,解构不是一个学派或一种方法,不是一种哲学或一种实践,而是正在发生的什么东西,一如某个文本的论点挖了自己的墙脚,或如“解构”(deconstruction)这个德里达在海德格尔文字中翻译Abbau和Destruktion这两个术语时偶尔引进的法语词,有了自己的鲜活生命,逃脱作者的控制,来指涉一个更为广泛的知识过程或运动,它虽然终结于20世纪,却并不意味着灯枯油尽。
关于解构,表述五花八门,一般将其表征为一种哲学立场、一种政治或思维策略以及一种阅读模式。文学或文学理论专业的学生,最感兴趣的无疑是它作为一种阅读和阐释方法的力量了。但是,倘若我们的目标是描述并评价文学研究中的解构实践,那么便有充分的理由先宕开一笔,暂从解构作为一种哲学策略说起,也许应当更确切地说,暂从解构作为哲学内部以及同哲学打交道的一种策略说起。
因为解构的实践既激发了哲学内部的剧烈纷争,又使哲学范畴或哲学把握世界的企图一败涂地。德里达描述过“解构的一个主要策略”:“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命题中,绝无两个对项的和平共处,只有森严的等级:一个单项在价值、逻辑等等方面统治着另一单项,高居发号施令的地位。解构要做的最重要的事,便是在一特定时机,把等级秩序颠倒过来。”
解构崛起于哲学,是针对哲学传统颗粒的哲学阅读,质疑其二元等级对立,诸如意义vs形式、灵魂vs肉体、内vs外、言语vs文字等等,探讨这些有模有样的结构如何被维护或依赖着它们的文本给事先解构了。
有鉴于雅克·德里达的哲学风格是仔细阅读文本,读大师们的资源,执目于其修辞策略和意识形态投资,因而他的著作深受文学师生们的欢迎。他们从中发现了两点:一是细读并不屈从于有机形式的意识形态观念,它们支撑着大多数广为传布的细读实践,如新批评;二是其显示出文本游戏冒着重要风险一一它们挑战的二元对立建构了最基本问题的思考,诚如我在第二章和第三章将表明的那样。
德里达的阅读,其目标不在于崇拜作品的艺术性和它们语义结构的复杂性,而在于抽绎出作品中相互矛盾的指意力量,对这些文本明察秋毫承担下来的虔诚和原则发难。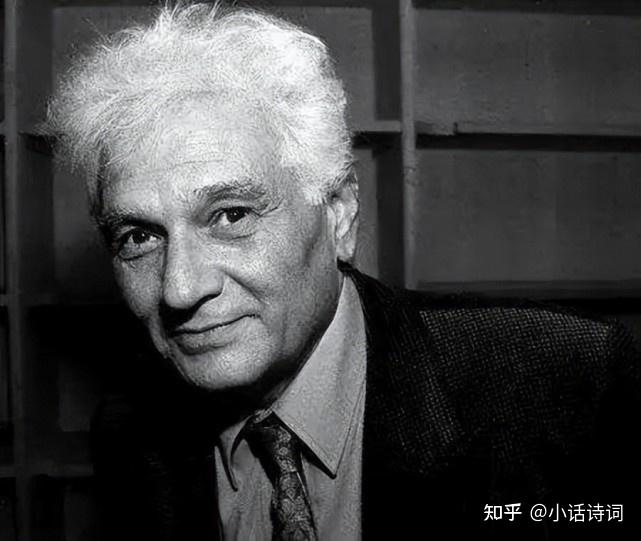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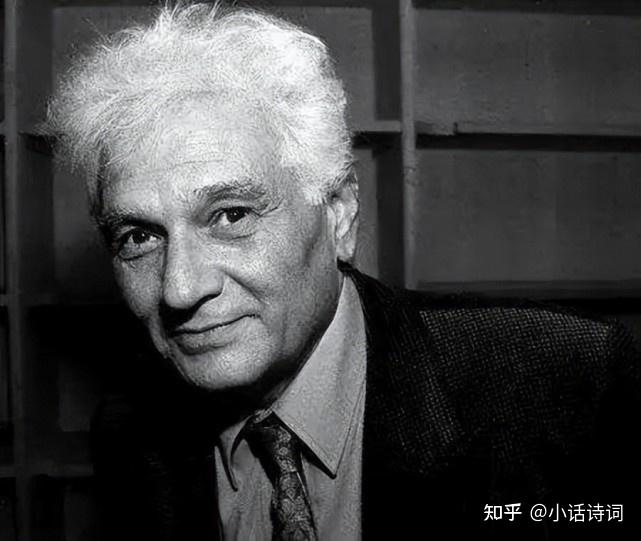 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
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
美国解构主义代表人物乔纳森·卡勒在《论解构》第一章探讨了解构主义同结构主义以及其他批评运动的关系。第二章叙述了德里达如何挑战哲学传统,以及解构阅读的策略特征。第三章具体讨论解构给文学研究提供了哪些可能性。
因为自《论解构》在1982年面世之后,有关解构的书陡增,不计其数。我们不妨来浏览一下以下材料:之后的22年里,德里达本人的文字包括30多本书,多不胜数的文章、讲演稿、序言和访谈。
在一段时间里,德里达的文字是有关“解构”这个术语的主要资源,但是解构早在1982年就已经参与到哲学、精神分析和文学研究中,以后更成为一个无比强大的知识范式,它对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各类领域产生的影响,标记了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生活。
“解构”这个词因此渐而被用来指涉一系列激进的理论工程,涉及的学科有法律、建筑、神学、女性主义、男女同性恋研究、伦理学与政治理论,且不论哲学、精神分析,以及文学和文化研究。虽然五花八门,但这些工程也“同仇敌忾”,一并对先前被视为上述学科基础的那些二元对立概念发难。
这个规划,加上“解构”这个术语本身的光华,使它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文化论争中大放异彩。但凡打开经典,站边妇女们的、少数族裔的、第三世界文化的,抑或拒绝高雅文化偏好大众文化的战斗,在形形色色的压力下,莫不抓住“解构”这个语词,来给各式各样的成就贴标签,他们认为是在打倒西方文明本身的成就。
而事实上,对于解构主义批评家们而言,他们虽然同情各种拓宽经典的运动,但又都被深深卷入高雅文化传统的文本里。从柏拉图到普鲁斯特,在他们看来都格外广博睿智,丰实且又锐利,这是先前的读者所未料及的。
他们很少会鼓动用肥皂剧来替代莎士比亚和康德,期望教授大众文化,很少用非西方文本来替代文化研究从业者撰写的西方传统历史批判著作。这些从业者视解构为洪水猛兽和精英的敌人,他们忠于高雅文化,纠缠在不知所云的哲学文本及其专门术语里,欣赏晦涩艰深。但是这都是语言的诱惑,在文化战争中,“解构”变成一把大刷子,涂抹掉学术著作中的一切创新点,又变成了攻击西方经典和既定价值的虚无主义速记。

关于解构西方文化的这类争执,今日似已相当少见。今天,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力量方兴未艾,产生了巨大的文化效应,一如大学里的阅读书目更替翻新,文学与哲学的分析模式也已全然不同。布什政府的所为,也让西方文化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声名狼藉,效果远甚于以往对其盲点和矛盾的一切批判分析,故与其驻留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有关“解构”一语的遗产里。
雅克·德里达本人在1982年之前的文字,已经涉及一大批文本和问题,如哲学、精神分析、美学和艺术批评,以及文学研究。但是这之后,他的文字涉及的范围和知识能量更叫人瞠目结舌。姑且列举若干吧。他冒险进入了这些领域:法律、宗教、友谊以及敌友之间的政治角色、马克思的遗产、欧洲的可能性、“无赖国家”概念、制度和哲学教学,以及他本人的传记。
不仅如此,德里达还写了大量文学评论,从莎士比亚写到策兰,尤其是着重探讨了波德莱尔、乔伊斯、蓬热、热内、布朗肖和策兰。这些文本谈不上是对二元等级对立的解构,也不是对这些二元对立的倒置和移位,诚如德雷克·阿特里奇一篇重要访谈的标题所示,它们探讨了“所谓文学的奇怪制度”。这些文章执目于文学的行为维度,即努力将其标举为一个单一事件,赋予文学以至高的样板权力,来言说一切理当成为民主标志的东西。
文学带着“秘密的诱惑”使我们激动,呼唤我们进行阐释,即便原本没有秘密,没有隐藏的答案。这些文章不是在阐释作品,而是在探索其最大风险和最广泛含义,以及最隐秘的语言游戏。
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德里达灵感的《文学的单一性》一书中,阿特里奇说:“过去35年里,德里达的著作构筑了我们时代最有意义、最广为传布、最有创意的文学探讨。”虽然迄今为止对这一宏论尚少有评价,也少有人深解其意。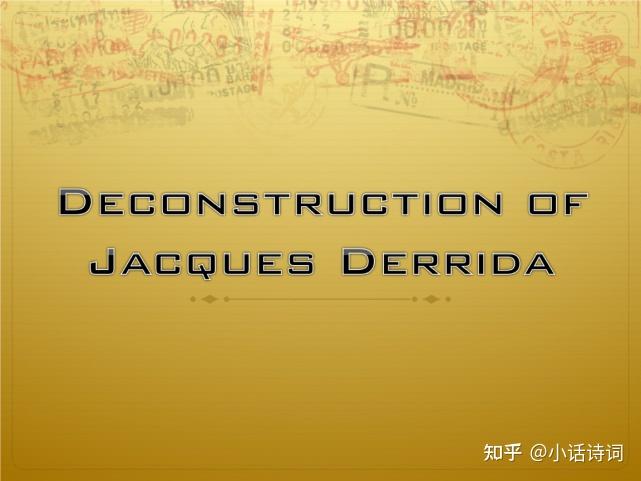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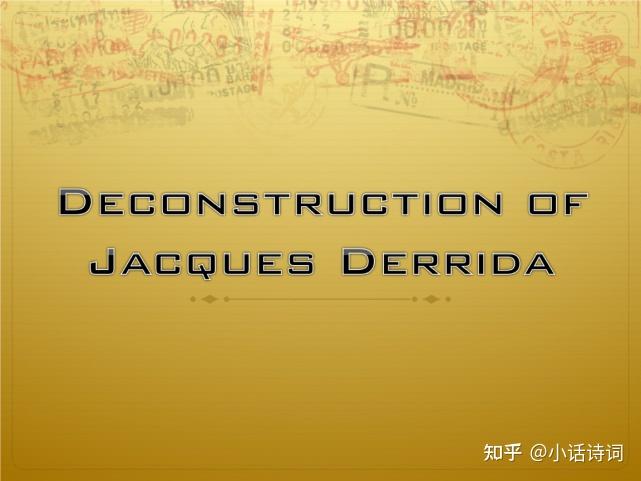
还有其他许多有关德里达的著述。其中两本尤其精彩和与众不同。一本是杰夫·本宁顿的《德里达数据库》,该书是对德里达思想的综述,德里达在每一页的底部刊出自传体的《割礼 忏悔》以示超越,由此两人合作出版了《雅克·德里达》一书。另一本是马丁·哈格伦德的《激进无神论:德里达与生命的时间》,该书将德里达对哲学传统的挑战,解释为对超验性的断然拒绝和对生存的充分肯定。
1982年以来,解构已深入了许多领域,但是在哲学内部,它依然是一个论争探讨的话题与资源。一方面,分析哲学家们普遍抵制解构,抵制德里达,甚至于走极端地将他排除出哲学,归入文学理论家一类。塞缪尔·C·韦勒的《作为分析哲学的解构》和戈顿·贝恩的《挤干去掉德里达水分:分析重申重复性》,成功地用分析哲学的术语重塑了德里达的论点。
而罗道尔夫·伽歇则决心将德里达从文学理论中拯救出来,在其《镜箔:德里达与反思的哲学》一书中,其弹精竭虑,成功将德里达表征为传统模式中的系统哲学家。在其他以德里达为哲学家的著作中,杰夫·本宁顿的《中断德里达》一书中有对德里达著作的一篇精彩的哲学分析。
在文学研究内部,解构今已广为传布,因此同解构相关的概念同样是四面八方传播开来。除了德里达本人关于文学的浩瀚文字尚未被批评实践充分吸收外,保罗·德曼的大量著述,虽然有很一大部分是在作者身后方才出版的,但是也变得唾手可得。
这些文章巩固了《论解构》中勾勒的一个独树一帜的解构传统,或者说,文学作品的修辞阅读传统。巴尔弗、布思、伯特、卡露斯、切斯、艾德尔曼、哈马歇、赫尔兹、雅各布斯、卡姆芙、雷德菲尔德、洛伊尔、特拉达和沃敏斯基等人的著作,皆为这一谱系的扛鼎之作。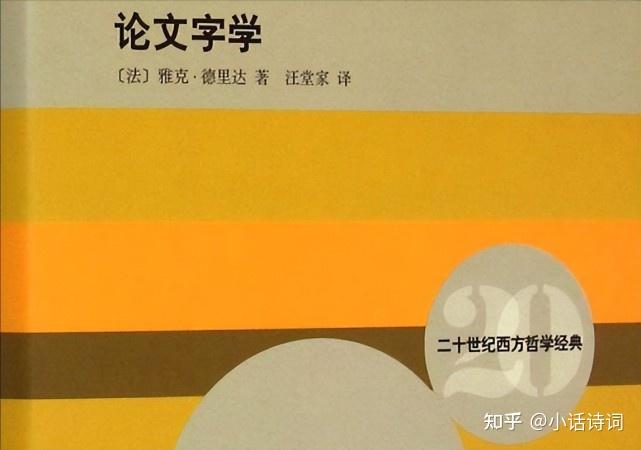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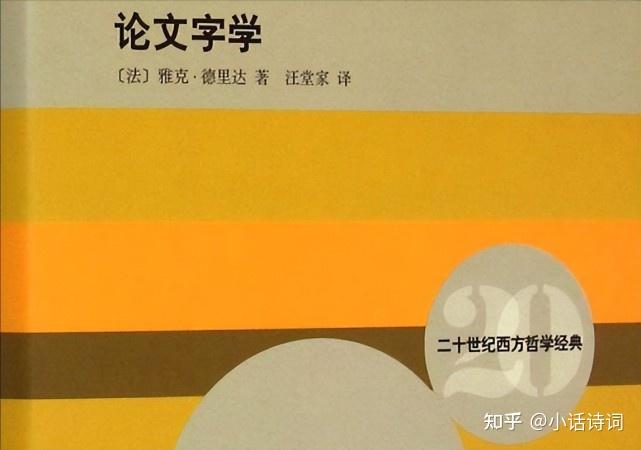
近年来,已经较少评论致力于表明文学作品如何颠覆了它们所依赖的前提,而是更多地卷人它们的哲学标的,如德曼《阅读的寓意》中评论卢梭的篇章所为。J.希利斯·米勒一向是个多产的批评家,其著作论及大量作家和主题,尤其是叙事和修辞策略。佳亚特里·斯皮沃克、霍米·巴巴、罗伯特·扬,以及其他论者,则阐明了后殖民研究的生产性,对解构活动保持了一份戒心。
芭芭拉·约翰逊,是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翻译家,最先将德里达解构主义译介到美国的学者之一。芭芭拉·约翰逊在其早期那些深刻且优雅的解构主义文献中对《论解构》已有高度评价,她一如既往,将研究领域拓宽到精神分析、妇女写作、女性主义、非裔美国文学以及文化研究。芭芭拉·约翰逊的两篇文章可以作为解构阅读的范本来加以引述,它们是《抒情诗与法律中的拟人论》和《沉默妒忌》。
前者出色地将德曼的拟人论修辞归拢一体,这对于抒情诗以及法律论争中拟人论活动的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确定法律将什么作为人一般来对待,法律给予哪一些实体或组织以人的权利,法律对于社会特权和资源分配的影响举足轻重。

芭芭拉·约翰逊的《沉默妒忌》读济慈的《希腊古瓮颂》,以“童贞未失的安静的新娘”一句,来对照简·坎皮恩的电影《钢琴课》以及电影的批评接受,以探索女性沉默的文化建构和审美化,探究它们如何成为女性价值的储存库。琼生得出的结论是,这部作品把妇女的沉默理想化了,结果是“它帮助文化,使之无从辨别她们的快感和侮辱”。这是《钢琴课》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及争论焦点。琼生的文章是解构阅读的一个精彩绝伦、洞烛幽微的范本,引申到了有关重大事件的形形色色的文化文本。
除了哲学与文学研究之外,解构的影响亦十分广泛。从最广泛意义上来说,它鼓励质疑一切探索领域的二元等级对立结构,专执于这些根基层面上的二元对立是不是,以及如何为它们被用来描述的现象所颠覆。
因而解构是一个有力的武器,对所谓的科学元语言发起总攻。所谓科学的元语言,指的是一系列术语和概念,它们被用来分析某个被认为外在于它们描述对象的领域。例如,某种精神分析理论,如何为它自称描述的压抑和愿望实现机制所构成,或为其所左右。
在文学与哲学研究之外,解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不是首先关注一个文本说了什么,而是首先看它如何维系与其所言的关系。解构凸显活跃在一切话语和话语实践中的修辞结构和行为效果,以其为特殊方式的话语解构经验。
因此,它支持鼓励形形色色学科的建构倾向:尝试表明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并非单纯诉诸经验,而是由概念网络和话语实践生产出来的。另一方面,解构思维作为对基础二元对立的批判探究,试图干涉和改变附着于特定术语上的价值,它不仅影响到如何阅读文本,而且影响到了一个学科的目标设定。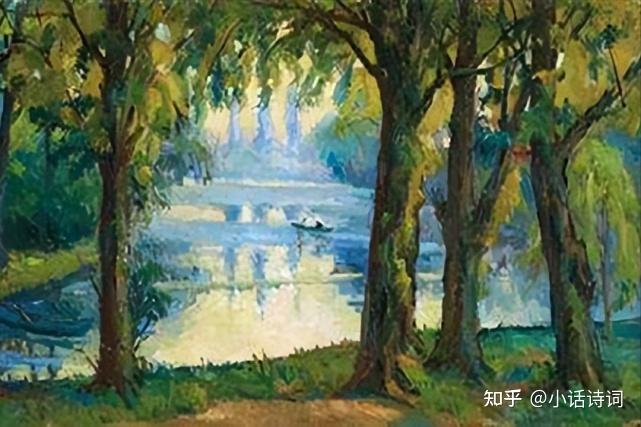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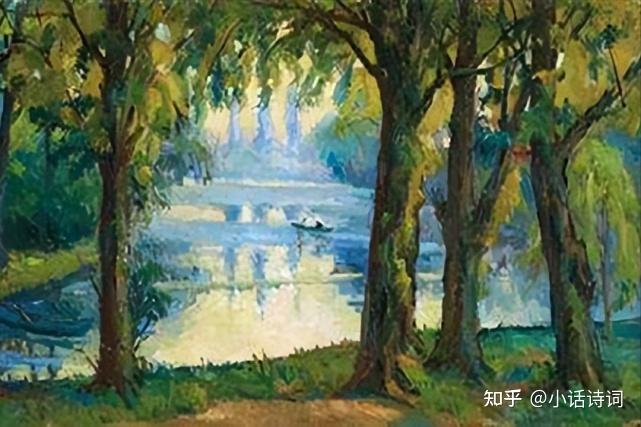
解构在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的声誉如日中天,随着之后其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广泛传播,它已经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成为对所谓天经地义范畴的一种批判,以及驱使你殚精竭虑去分析一个特定学科中指代逻辑的动力。即便其结果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恶化局势,激发出更多的问题和疑云。
故此,它联手其他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思潮,来激发对既定范畴和经典的怀疑,进而挑战客观性。尼古拉斯·洛伊尔主编的《解构:读者指南》是关于解构的各式宣言中的一部杰出导论,诸多名家撰稿,在“解构与……”的类别下,其讨论的话题极其广泛,包括解构与文化研究、女性主义、小说、电影、阐释学、爱情、一首诗、后殖民、精神分析、技术,以及编织。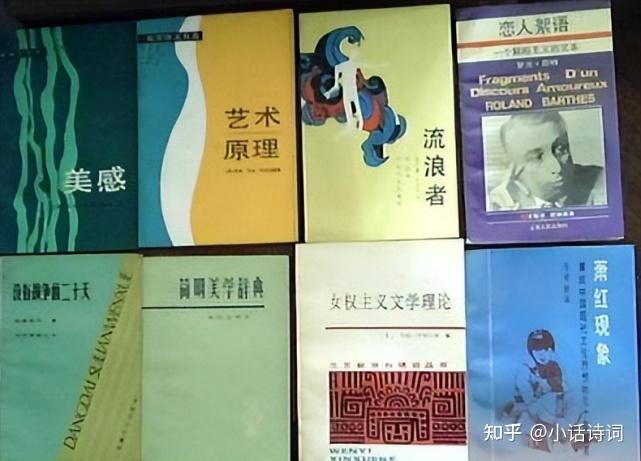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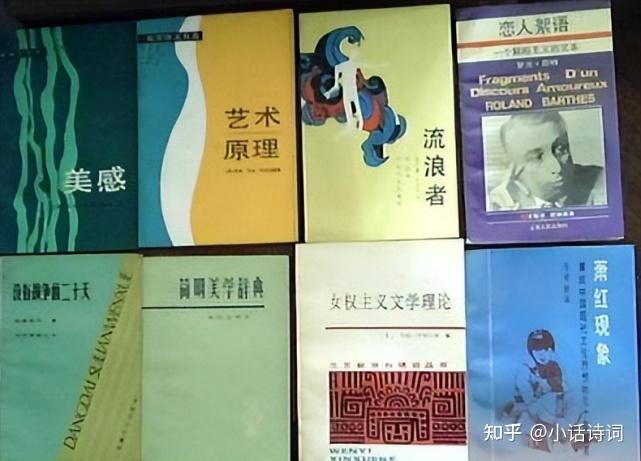
(一)女性主义,性别研究与酷儿理论
虽然女性主义一直对解构主义疑神疑鬼,觉得它是种典型的男性消遣、抽象消闲,让思想千篇一律,比如,其实际上有意否认女性经验的权威性;但是,许多女性主义思潮始终支持解构男人和女人这个二元对立,支持批判身份的本质主义概念。佳亚特里·斯皮沃克这位马克思主义者和后殖民批评家,始终强烈呼吁将解构与女性主义及其他热点问题连接起来。
但是解构最杰出的代表还是朱迪斯·巴特勒,朱迪斯·巴特勒是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修辞与比较文学系教授。她将德里达与福柯拉进了她有关性别与身份的理论工程。经常有人说,女性主义政治追求一种妇女的身份,就是说,这一身份是产物或结果,而不是行动资源。
但是《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身体的颠覆》《至关重要的身体》以及其他著作,则挑战了这一观念,并发展出一种性别和性认同的操演概念。它先是师法J·L·奥斯丁的行为句概念,由此生发出一系列相关实体对象,与此同时也借鉴了德里达有关行为句重复性的论点,正是它成就了巴特勒性别概念的这一重要分支。巴特勒的著作在诠释当代男女同性恋研究以及女性主义方面功不可没。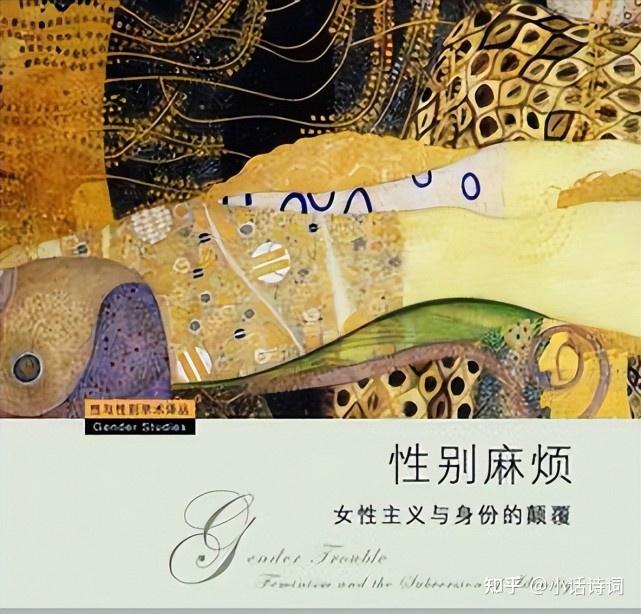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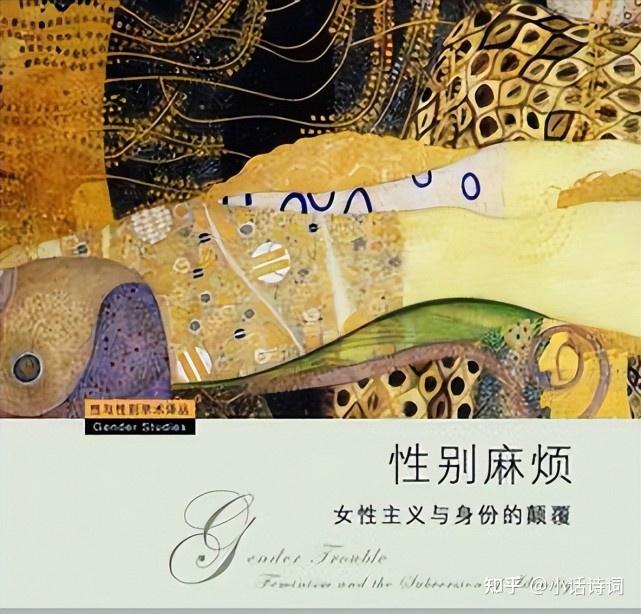
(二)宗教 神学
解构作为对形而上学的批判,特别是对在场的形而上学以及西方文化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似乎注定是反神学事业的,是对依然在支撑我们思维的神学母题和结构的一种批判。但是,这一揭示西方世俗文化,特别是哲学之隐秘神学结构的心志,也导致了此种观念的兴起,那就是解构乃是否定神学的一个版式。
有些学者,如约翰·卡普托,在德里达思想中高扬弥赛亚概念,试图发掘一种德里达式的神学概念,将延宕的母题同等待弥赛亚降临联系起来,后者是基督教末世学的标识。其进而从论证解构包含了宗教的母题和对得意扬扬世俗化理性的批判,发展到坚信在“没有宗教的宗教”和“没有弥赛亚的弥赛亚式”中,解构赋予我们的不是宗教的不可能性,而是一种具有否定性的宗教,一种没有真实宗教种种缺陷的宗教。
但是德里达在弥赛亚式和弥赛亚主义之间作出的区分至关重要,这并不是吹毛求疵:前者是分析某个等待和延宕的结构,后者是真实弥赛亚的信仰。
对解构与宗教的讨论似乎兵分两路:一路将宗教引入德里达与解构,最终阐明解构是具有它自身结构和担当的宗教,从而促生一种保存了现代宗教担当中最有价值的东西的伦理学;另一路则将解构引入神学,以使它更具哲学的复杂性,更为精致,也更有责任感。
是不是解构非得标举无神论,否则便无以为继?抑或它是不是能在神学语境内部展开,以生产一种能够“逃避”哲学的神学?解构与宗教的第三条路径是,运用解构,至少是立足于德里达的早期著作,来批判宗教和神学。
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它通常缺席文学。在德里达为他与吉安尼·瓦蒂莫合编的《宗教》一书贡献的长文中,德里达并非全然将神学视为宗教本身,而是更多地将其视为某种社会和精神现象,表明运用解构来谈宗教问题,确实是有所不同的。但是马丁·哈格伦德的《激进无神论:德里达与生命的时间》则明确反驳了从宗教中捕捉解构的企图。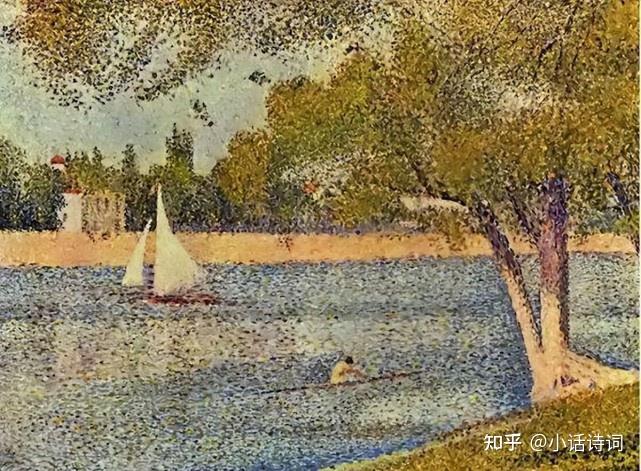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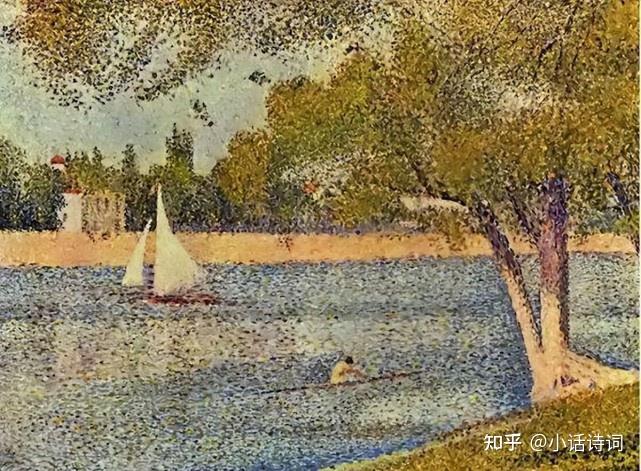
(三)建筑
解构与建筑?这个结合有点匪夷所思。不过“解构”这个语词已经包括了构造的意思,并意在分析一个结构如何被结构起来。为什么解构就不能与建筑领域中的空间、功能和装饰思考联系起来呢?
1985年,世界著名建筑评论家、设计师伯纳德·屈米邀请德里达合作设计了拉维列特公园的一个区域。拉维列特是一个大型公园,园内有多处时新博物馆和展览空间,形形色色的设计理论就在这里登台亮相。在屈米的计划中,一系列红色的立方体空间,即设计者所谓的follies,将被安置在特定的点上,每一个立方体通过“偏差”,变形为一个folly,即结构的爆炸和消费。不同性质和逻辑的结构相互叠加,颠覆了整体的概念。
设计不仅否定了与语境的关系一一那可通常是建筑存在的理由一一而且位移和放开意义,否定了“建筑作为人文主义思想避风港的象征储存库”。屈米说:“它的目标是一种什么意义也没有的建筑。”德里达与彼得·埃森曼进行了合作设计,然而因一项原则性决定,方案未被施行。
1988年,美国建筑师和评论家菲利普·约翰逊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组织了一次展览,题为“解构主义建筑”。由是观之,建筑的解构之所以成为可能,并非由于其是解构主义哲学的派生物,而在于它能够动摇我们关于形式的思考。这一建筑通过揭示隐藏在传统形式中的不稳定性和进退失据困境,来进行策反和颠覆活动,于熟悉中见陌生。
 洛杉矶迪斯尼音乐厅是一座巨大的解构主义建筑
洛杉矶迪斯尼音乐厅是一座巨大的解构主义建筑
(四)政治、法律、伦理学
解构与政治的关系又当何论?比如,解构是否拥有一种政治学,抑或它是一种可以随心所欲、因地制宜,采用政治的一切不可能性来加以推动的思想?杰夫·本宁顿注意到,由于德里达的哲学著作如此激进,以至于在英语世界中有一种看法,认为它可以促生一种同样激进的政治或解构主义政治学,如是人们可以挑剔德里达,指责他辜负了某些人的期望,未能对政治与现实一视同仁。
德里达在许多政治问题和论争中固然立场鲜明,可是似这般模样投身左派,或扮演左派,却还是叫许多人失望,他们追求另一个秩序的激进政治,期望改变世界。
德里达关于政治的著述十分广博。一方面有直接的政治话题,诸如种族隔离、移民法、死刑、欧洲一体化。另一方面又有最广泛意义上的政治理论,如:《友谊政治学》通过敌友问题来深入政治和民主;《马克思的幽灵》质问了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以及它在后马克思主义世界中的重要地位;《独立宣言》则令人信服地将《美国独立宣言》读作歪曲基本行为的范本,其间语言的行为维度和陈述维度无以两相契合。
通观德里达的著作,交织着对宣言概括之决议和民主的一种反思:“凡解构必有民主,凡民主必有解构。”一个决议之所以是决议,前提是它不能被计划,而是发生在一个无以决断的情境之中。它必须打断确认,而确认依然是它可能性的条件。至于民主,一个基于计数的结构一计数异常一则是这样一个概念:我们以它的名义评估每一种民主的确认,正是以“即将来临的民主”的名义,我们解构一切给定的民主概念。
解构与政治是一个热门话题,相关著述数不胜数。本宁顿的《法规:解构的政治学》和理查·比尔兹沃斯《德里达与政治问题》是此一话题的重要著作。另一方面,欧洲大陆哲学传统中对政治学的解构工程,则由菲利普·拉库拉巴特和让吕克·南希、厄内斯特·拉克劳和查特尔·墨菲开拓了一种因引入解构而变调的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美国政治科学家威廉·康诺利、比尔·马丁、威廉·科列特以及其他学者,则在政治科学话语中,引入了对差异悖论的思考,以及对二元对立等级的解构。同样,我们还应在解构与政治的标题下,列人斯皮沃克、霍米·巴巴和罗伯特·扬的后殖民研究文字,以及朱迪斯·巴特勒《激动的话语》中对仇恨话语的质问

(五)法律
在法律领域,批判法律研究运动聚焦于法律教义内部原则与反原则之间的冲突,它与解构多有类似:批判公共与私人、本质与偶然、内容与形式等一系列二元对立,它们都是法律领域的基础所在。同时阐明法律教义与论据是意在掩盖矛盾,而矛盾依然重新显现出来。在这一领域里德里达本人的文字又有所不同,如他的《法律的力量:权威的神秘基础》就探讨了根本意义上的暴力和正义问题何以是无法解决的。
正义问题素来是解构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导致了解构与伦理学的论争。有鉴于解构总使人联想到蔑视既定规范与传统,拥抱不辨善恶的尼采轨迹,其与伦理学似乎最是遥远。伦理学概念本身,连带法律、责任、义务以及决定等概念,都来自形而上学,解构如何独能绕过这些问题不作诘难?但是我将这一点构想为义不容辞的必然,这个事实本身也使我们有可能来询问解构背后的动机所在。这里运行的是哪一种必然、义务或承诺,是伦理学的抑或不是?由此来驱动解构,或者让我们责无旁贷地关注正在发生的各种解构是什么?
是哪一种价值和义务,驱使或迫使我们来行动?这是一个伦理学问题,或者说,就是伦理学的问题。就解构的例子来看,伦理学问题直达其方法论的核心。是什么在驱动解构?我们为什么关心它?“因为我们别无选择,”西蒙·克里奇利回答说,“统治着解构的必然性来自整个儿的他者,命数女神阿南刻,在她面前,我无法拒绝,凡我自由心愿,皆为正义所抛弃。作如是言,我相信我是追随德里达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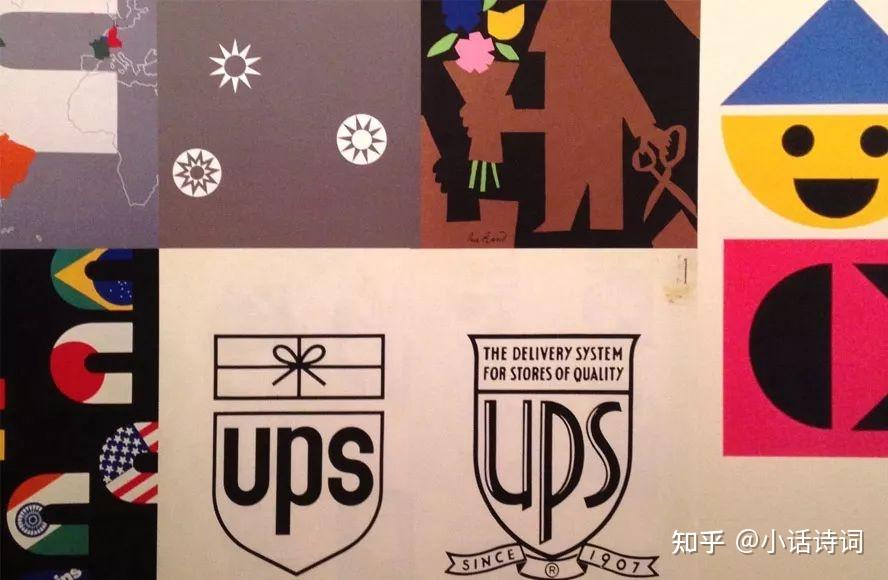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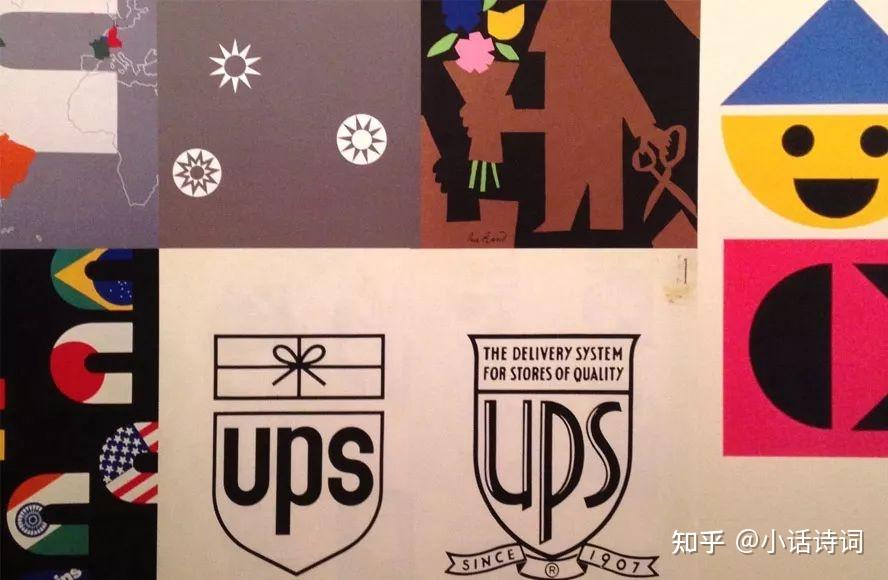
近年来,解构与伦理学或者伦理问题的关系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这也许并不奇怪。一方面,论者探究驱动解构的要求属于何种性质,是渴望正义呢,还是尊重文本表征的他者性,抑或致敬他人的他者性。另一方面,德里达与伊曼努尔·列维纳斯还有一场延续了数十年的对话,其代表着德里达对伦理转换问题最直接的参与。
雅克·德里达说,列维纳斯的思想为我们唤醒了一个“超越和先于我的自由的‘无限’责任”的概念。如杰夫·本宁顿和其他论者所言,德里达与列维纳斯的对话,批判了将伦理学确立为先于本体论之第一哲学的企图,而本体论总是有将上帝树立为绝对的他异性,树立为伦理学根基上他者的单一面真理的风险。以他者为总是非绝对的,伦理学是没有可能的,尝试某种没有伦理学的伦理学,这正是落在解构身上的使命。
有一句玩笑话: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做哲学或进行广义的创造活动:一种是解构式的,另一种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即,一个写作者,是否受过解构思维的洗礼,将是两种人。
因为,一个受过解构洗礼的人,他必须:把一切现成的东西,都还原为原初生成的东西,是从无到有的思维,其它的思维是从有到有的思维。你必须把这个既成的东西,以从无到有的方式,以自己的方式重构出来。
解构,因此,不是否定,恰好是肯定,如同上面有人说的,是对于既有之物的肯定,使之可以重新发生。
解构,因此面对的是结构的封闭,任何结构都要求自身的完整性,而且以权力或暴力,来保证自己的结构,这样就形成了封闭。因为并没有结构——固定的同一性的某种不变的结构,而是可以重组,不断的生成。因此,结构的封闭与游戏的敞开,或者游戏的重新发生,就是解构要做的解放工作,以及对于他者的发现。
每一次都要发现他者,都要重构这个文本,使之重新发生,这就是解构的魅力与要求。
最近更新科技资讯
- 22年过去了,《透明人》依然是尺度最大的科幻电影,没有之一
- 人类基因编辑技术及其伦理问题
- 不吹不黑,五阿哥版的《嫌疑人》能过及格线
- 论Lacan心理公众号的“双标”特质
- 猎罪图鉴:犯罪实录 女性伦理
- 清入关的第一位皇帝是谁,清朝入关后有几位皇帝?
- 描写露台的优美句子
- 谭德晶:论迎春悲剧的叙事艺术
- 中秋节的好词好句
- 《三夫》:一女侍三夫,尺度最大的华语片要来了
- 赛博朋克的未来,在这里
- 文件1091/721/2A:反概念武器实体的一封信件
- 尤战生:哥伦比亚大学点点滴滴
- 韩国最具独特魅力的男演员(安在旭主演的电视剧有哪些)
- 乃至造句
- 请保护好我们的医生,他们太难了
- GCLL06-土木工程的伦理问题-以湖南凤凰县沱江大桥大坍塌事故为例
- 黄金宝典:九年级道德与法治核心考点必背篇
- 【我心中的孔子】伟大的孔子 思想的泰山
- CAMKII-δ9拮抗剂及其用途
- 选粹 | 郑玉双:法教义学如何应对科技挑战?——以自动驾驶汽车为例
- 苍井空37岁宛若少女,携子送祝福遭热讽,下架所有视频母爱无私
- 日韩新加坡怎么对待影视剧中的裸露镜头
- 中西方文化中的颜色词
- 土豪家的美女摸乳师——关于电影《美人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