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机访问:wap.265xx.com
手机访问:wap.265xx.com技术伦理:一切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生命的本体
未来只有一个吗?
乔布斯在自传中写到,他嗨大麻之后听巴赫音乐的感觉。他说:“我站在草原的中央,感觉到所有的草都在随着我舞蹈和歌唱,在那个时刻我看到了未来,我知道我可以让所有人随着我的心意游动!”
彼时他感受到了跟万事万物万体之间全然的连接。他也感受到了塑造这种连接的渠道。那就是苹果的起点。那是乔布斯的场景。他的下意识完整地体现为“自我”跟“江山河流”的连接。
费俊是中央美术学院新媒体专业的导师。他是关于未来和流动媒体的哲学家。他是从哲学的高度,从表达的本质和审美的思辨去思考新媒体。在中国,新媒体的领域跟创业息息相关,跟今天所有的金融产业以及信息的分享息息相关。费俊从伦理和审美的高度在思考此时此刻的人类对未来的表达。
我们会分几期来分享费俊对“技术伦理”这个命题的深度阐释。
在以下的几个月中,我们会不断展开关于“未来学”的讨论。
——冰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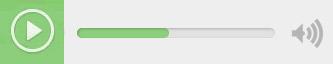
费俊
中央美术学院数码媒体工作室副教授
2015,2017届醴斯人文学院导师
2016
1
过去的二十几年,我一直在追求同一件事情:
我在不断地思考和结合新的技术和艺术,靠个人实践创造出酷炫的、叫“声光电”的东西,让人们产生对新媒体的兴趣和理解。
我始终是这样一个布道者。
过去的两年,我进入了之前从没有预想过的角色。从去年策划“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开始,我经历了巨大的转向。我开始更多地从人的角度去思考。
在我看来,新媒体对于传统媒体具有很强的颠覆性和革命性,并且具备人性的释放的无限能力。今天的技术不再是高门槛的权力话语。每个人都可以利用新媒介来进表达,思考和创造。
在这一年多的工作里我深刻感受到的是 |一切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还是生命本体 |。尤其在技术失控的年代,技术有它的伦理问题,在这些伦理问题面前,每一个人不得不重新思考生命是怎么回事,生命会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技术的发展,使得每一个人跟技术之间的理解被切断了:如果说1000年前我们的祖先能够理解他手里的的每一种技术,比如说榔头,斧子,它由什么构成,怎么被制作出来,使用它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但是今天每个人手里拿着的手机都不知道是怎么被制造的,和它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齐泽克有过一段描述,他说 | 哲学传统意义上是哲学家的思考,而今天似乎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哲学家,才能够理解身边发生的事情 | 。
2
以下是我的几点结论:
第一: “展览”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一种过气的交流方式。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这种白盒子式的载体本身与今天的时代之间是脱节的,但它依然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机器,是一个最容易传播用户体验的机器。所以第一个我带出来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还是不得不在一个白盒子里做展览,有什么方式能够去拓展这个空间?
第二个问题是说:基于这样一个固定的”白盒子“空间的交流方式,有什么方法能使这个交流变得更有效?
作为观众,我看过无数的展览。我们经常忽视一些观众听起来似乎很愚昧的回应,说”这个展览我看不懂”。每每碰到这样的观众,包括我自己的母亲问我的时候,我都很汗颜。
我们善于说:“你不懂语境”。我们习惯性地把观众的困惑和不解当成理所当然,但我们忽略了一个朴实的事实:我们并没有花足够多的精力在展览的解读和沟通上。尤其是媒体艺术这种技术性强的作品中,观众之所以不理解,是因为确实不理解它产生的上下文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办一个展览最重要的是如何建立展览和观众之间的相关性。
如何建立作品与话题间的相关性?如何建立观众与作品间的相关性?是这个展览中最核心的工作,也是难度最高的工作。
我们有一个展览的宣传影片,当时北广传媒(北京拥有很多地铁屏幕以及楼宇屏幕的一家公司)答应用他们的屏幕作为我们展览的一个公共载体。当我把文件发过去的时候,他给我回复了两次电话,说你的文件在传输过程中损坏掉。后来我明白他说的损坏是什么意思,是因为他从来 没见过这么低精度的一个让人不适的视频。最终也是由于这条原因,他拒绝了在地铁上播放。
影片最前面提出的几个问题,貌似并非学术问题。比如说“机器人会不会取代我的工作”,比如说“我的孩子要不要做基因增强”,我觉得 | 这些都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就是学术问题,就是哲学问题 |。
我们把语言降到最能理解的程度来建立强相关性。这是从一开始我们就设定的调性:我希望它是基于学术背景研究出来的呈现,同时它一定是面向普通人的。
这些面向公众的问题传播的是最主要的信息。
为什么我们会花将近半年的时间来做文献研究?这个研究最终的成果之一就是展览现场150米长的文献墙。某种意义上,作品可以说是文献墙的陪衬,而所有展出的艺术家的作品,是顺着文献的思路来构成的。
我们对科技伦理的探求分成了五个大的话题,包括元科学,大数据,混合现实,生物基因,还有人工智能等。每一个话题在现场都有丰富详尽的百科式的文献呈现,就是为了能够帮助在现场的观众,建立起作品所讨论的问题是什么的认识,建立起对这些技术术语或者哲学术语的一个浅薄的理解。

大云图
文献除了从学术的哲学书籍以及行业的数据库里面截取出来的,也还包含了很多像纪录片,以及电影中对于这些概念的一些描述。与这个文献墙配套的是一套我称为知识包的文献,这也许是这个展览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这套文献中包括所有和这个展览相关的论文、百科册子、知识图谱、作品介绍以及文献海报等。
以上是最大的一个海报,我们称之为大云图。它把所有展览相关的概念和核心的哲学家用信息可视化的方式呈现出来。
3
技术伦理貌似是一个西方哲学的话题,但我们发现其实中国早就存在这样的话题,中国形成了基于人伦、天伦的处世原则,并架构了基于物理、道理、天理的认知系统,所以“伦理”这个词本身在中文中就有非常丰富的含义。中国哲学家们关于“技”与“道”的辩证正是对于技术与伦理的哲学思辨。
庄子曾鲜明地反对被机心所裹挟的“技”,而推崇道法自然的发展观和价值观。在西方,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指出 | 我们人类认识世界的两类驱力:由概念(认识论)或由工具(科学技术)驱动: “如果我们人类的探索和发现是由‘概念’所驱动,那我们就趋于用新的?角度解释旧的东西;如果是被‘工具’所驱动,我们则会用旧有观念解释新发现与新创造出来的东西 |。” 就像我的母亲,会用以前的电话来理解今天的手机,由于她在认知层面上没有新的发展,总会用旧的经验,旧的知识方式来解释今天的东西,那毫无疑问,不仅是解释不通,其实会阻碍发展。
这就是为什么概念的发展,或者说关于伦理的讨论,对技术本身的发展是有正向的作用,同时很大程度上就像齐泽克谈到:“伦理中的‘应该(ought)’并不是通往现代科学之路上的绊脚?,而是其指导。”
在这个展览里面,技术伦理是一个泛的话题,我们从五个角度来对它进行梳理,但确实通过很多作品提炼出了很多关键词,比如说数据隐私,数据宗教,数据遗产,机器觉醒,意识上传,赛博格,人机合体,基因改写,包括基因物种的不平等,还有现实虚拟化等等。
这些词其实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已经多多少少能够从生活中感受到,而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人类所拥有的解释系统在这些话题前面几乎完全失效。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法律。那就讲一个有趣的故事:我的某友由于不孕的原因,希望去找到有人捐献的卵子,大家知道捐献精子捐献卵子,是一个已经非常成熟的科学技术,但后来发现在中国捐献冷冻卵子这件事情是不合法的,他就很诧异为什么精子是合法的,卵子是不合法的。似乎人们认为捐献精子并不违反伦理问题,等于它帮助卵子获得了生命。但是捐献卵子就像捐献了母体一样。就像这样的法律,我们今天早已经越过捐献卵子的阶段了,可以直接做基因编辑,来进行人工授精等等或者说基因改写的方式,其实这种法律系统是完全没有办法去适应技术的快速迭代的问题,像这样的问题非常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技术伦理的话题不再是特定范畴的专业话题,而是一个关乎每个自然人的普世话题。
今天我们关注技术伦理,谈的不仅是未来,也是现在。
我们已经有太多由于技术所导致的伦理问题,包括环境中的各种问题。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环境污染所引发的自然灾害等危机面前处在一个崩溃的边缘。
上一篇:好看的免费电影推荐100部
下一篇:有什么老的经典的电影,都是名演员的?
最近更新娱乐资讯
- 获奖影评赏析|《阿丽塔·战斗天使》
- 人生必看十部好看的纪录片(十部必看的现实主义纪录片)
- 日本十大禁欲动漫盘点:唯美霸道下的污镜头
- 墨西哥大麻即将合法化,美媒:美国夹在两个“卖大麻的邻居”之间
- “和合”文化背景下昭君文化的价值生成
- 马来酸阿法替尼片人体生物等效性试验
- 原创《满城尽带黄金甲》:喧哗与沉静的戏台,道德与伦理的悲歌
- 裴旖旎
- 隐适美附件又掉了,从第一天掉了2颗,第二天掉了1颗,今晚我还戴牙套吗?
- 电视剧《最美的青春》:好作品是如何炼就的
- 狗头萝莉出摊卖煎饼大家怎么看?
- 记者的职业伦理:我该何时放下相机
- 绝命毒师电影,「蚁人」改造DNA,首部Netflix华语剧...10月流媒体片单
- 这是一部非常独特的「成人动画」,少儿不宜
- 高分电影推荐!六部直击人性黑暗面的韩国片!部部引人深省!
- 2022天津解放军464医院整形美容中心整形价格表(价目表)全新发布
- 精 [电影推荐]一再婚女人因拯救女儿,让两个家庭面临人性考验,此电影令人感动
- 缓冲晶体溶液与生理盐水对重症监护病房患者急性肾损伤的影响:SPLIT随机临床试验
- 未成年人千万别看这部片子,简直太变态了!!!
- 生态在文学中的位置
- 与3800多名女性发生过关系,世界小电影之王,终于那啥了
- 新加坡电影《爸妈不在家》爆冷获多项金马奖
- 调查称52%受访者认为国产电影色情暴力问题严重
- 红楼梦初中读书笔记
- 家庭伦理剧,小品剧本《家庭矛盾》








